老人花50年时间
用废品建成教堂
在西班牙一个叫mejorada delcampo的小镇上,有一座用“垃圾”修建起来的教堂。这座教堂将近40米高,出自一个西班牙老人之手,他靠着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花费53年的时间,一砖一瓦修筑。目前,教堂仍未完工,老人也已90岁高龄,但他仍在坚持。
1963年,他打下了教堂的第一块基石,建筑的原材料,是他收集来的各种废材、垃圾。教堂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有回廊、穹顶。
这是老人修建的教堂

老人的真容

为老人点108赞
奶牛其实喜欢“宅”
人们通常认为,放养的奶牛会比较自然,生活状态也会更放松,因此奶质会更好。但日本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奶牛其实不喜欢放养,更喜欢圈养。
据日本《农业新闻》网站近日报道,日本农研机构进行了一项长达半年的研究,调查了16头黑白花牛在放养和圈养条件下,它们尿液中的皮质醇浓度。这种黑白花牛是一种体形大、分布广、产奶量很高的奶牛品种。而皮质醇则是肾上腺在应激反应里产生的一种类激素,它能反映黑白花牛的压力水平。研究人员总共检测了400多次这些牛在放养和圈养条件下的尿液皮质醇浓度。结果发现,在放养情况下,这些奶牛的尿液皮质醇浓度比在圈养时要高,而且温度和湿度越高,这种倾向越明显,表明它们的压力也越大。
小编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啊~
涨知识啊有没有~
28年留起19公斤长发
美国人Asha Mandela今年50岁,来自佛罗里达州,是世界上头发最长的女人。她如今嫁给了一名来自肯尼亚的发型设计师Emmanuel Chege,两人可谓是天作之合。
Asha Mandela的头发长约16.8米(55英尺),比伦敦巴士还要长,重约19公斤。尽管头发已快压垮她的身体,但这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发誓永远不会剪掉头发。
28年前,Asha Mandela称自己听到“心灵的召唤”,于是开始留起了长发。2009年,亚莎的Asha Mandela就已经达到将近6米,她每次洗完头发晾干需要花费2天的时间,而且还必须要用婴儿吊索携带才行。
Asha Mandela说,“医生认为我的头发太长、太重,我的脖子快撑不住了,还可能压垮我的脊柱,引起痉挛和瘫痪,都建议我剪掉头发,但头发是我的生命,剪掉这一头长发等于让我自杀。”

这头发真是长啊~
有图头真相
现在再看看国内的奇闻
百岁灵芝重达10.72斤
“这么大的野生灵芝,还是第一次看到,真是太罕见了!”近日,湖南桂东县新坊乡村民陈远爬山游玩时,在该县槽里与株洲炎陵县交界处的一颗百年大树下,意外发现一颗野生大灵芝。
该灵芝菌盖很粗糙,上面有大小不一的小灵芝,菌表面呈深褐色。经测量,灵芝长74厘米、宽39厘米、高15厘米,重达10.72斤。所见之人,无不称奇。
该县农业部门有关专家介绍,野生灵芝对海拔高度、空气、温度、适度等生长的环境要求苛刻,主要生长在深山枯树根上。经鉴定,该灵芝属于木灵芝,无药用价值,年龄在100年以上,形状巨大,极为罕见。这也是迄今为止桂东境内发现的最大野生灵芝,有很高的收藏和观赏价值。
神秘黑洞?5万多斤鱼一夜消失
2016年3月29日,广西桂平市白沙镇第三初级中学附近,一个鱼塘出现了一个深坑,5万斤鱼被卷入坑中,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坑直径达四五米,呈椭圆形,坑壁与水面几乎垂直。记者设法靠近坑壁,只见下面七八米处形成一个水潭,扔一块石头进去,里面发出“叮咚”的声响,深浅难测。
据看守鱼塘的杨双贤介绍,从鱼塘塌陷到水面消失,仅仅数小时。鱼塘不远处就是2个巨大的采石挖出来的巨大“天坑”,坑底有一汪绿色的水。村民怀疑,采石场为了开采不停地抽水,造成了塌陷。有工人表示,两年前,靠近采石场的地里就不断发生塌陷,每次事发后,采石场就来填埋,但开采时抽出的水一直排放在附近地里,塌方也此起彼伏。调查得知,从2014年至今,以鱼塘为中心,周边一公里范围内已发现约50个塌陷坑。这个坑深度六七十米,面积有上万平方米。专家组给出的处理意见是,先对塌陷的鱼塘进行填埋,以防发生灾害。

看完了,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
都可以留言~

你们听说过哪些关于黄河的奇闻异事,历史故事?葭明通来说一段江苏徐州丰县废黄河变果园的历史故事吧!这个戈壁滩是怎么来的呢?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大沙河。起码应该有很多会读书懂科学的人来做这些工作才好!普通的农民群众是做不来这种工作的。然后就到了1957年!一致认为在“大沙河”应该直接种果树,尤其苹果树,不用搞什么防护林然后再造良田种庄稼的,不划算。遗惠今日!起码!在那个特殊年代,丰县征服了废黄河“小戈壁滩”,可以类比大寨梯田!
那是一个清晨,二叔去黄河边,取昨天晚上下好的网。让他意外的是,网里一条鱼也没有。却有一个透明的,乒乓球大小的物体。二叔有些好奇,用手指戳戳,感觉粘乎乎的。放在鼻子下面闻闻,有一股腥臭味,差点吐出来。
二叔很恼火,想把这个球状生物给扔了。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因为这个球状生物是活的,会扭来扭去。身体一会儿圆,一会儿扁,一会儿条。二叔看着有趣,就留了下来。
家中有个空置的水缸,二叔往里面倒了多半缸水,就把球状生物养在了里面。也许是怕太突兀了,还扔了五、六尾鲤鱼在里面。
二叔要忙去农活,一直到天擦黑,才回到了家里。想着早上捞的球状生物,便来到了水缸前。这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当真是吓了一跳。缸里的水,一片殷红。那生物倒还在缸里,只不过,已经变得有碗口那么大。缸里的五、六尾鲤鱼却只剩下了骨架,沉在了缸底。
二叔有些吃惊。这玩意儿,还能吃活鱼?他想了想,去厨下又捞了尾鲤鱼,投入了缸里。鲤鱼入缸,自由自在的游动着。没过多久,那个碗口大的生物,慢慢凑了过来,一下子便贴在了鲤鱼的身上。那鲤鱼拼命摆动,哪里挣脱的开?也就是眨眼睛的工夫,就被吞噬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缸里的水更是一片血红。
二叔倒抽了口冷气,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时,院里的长辈叫他去吃晚饭,他就暂时把这事儿给搁下了。等二叔再次想到这球状生物,已是第二天的晌午了。不知怎地,他心里有些发毛,人来到缸前,不禁又大吃一惊!
缸里只残留了一个篮球大小的透明膜儿,从中间撕裂了一个大洞,倒像是蜕下的皮。这玩意儿难道是跑了?二叔挠了挠头,在院里搜寻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也只好作罢了。
过了三、五天,二叔就把这事儿抛在了脑后。直到他有天傍晚收工回来,见邻居老王家门口,围了一大圈人。原来是老王媳妇儿站在门外“骂大街”,他才觉得是出了祸事!
老王家里,养了多年的一条黄狗。不吱声不吱气的,被吃得只剩下了骨架。老王媳妇儿那是一个泼辣女人,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这才站在自家门前破口大骂。二叔挤进了人群,看见了地上的黄狗骨架,打了个冷战。心头突突的乱跳,张嘴想说些什么,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二叔低着头,进了家门,他的心里很乱。第一,他不能确定,吃掉黄狗的,就是那个玩意儿。第二,就算说出来了,村里会有人信吗?第三,那玩意儿是他带回村里的,吃了一条黄狗事小,那老王媳妇儿却是出了名的泼辣货,二叔怎敢平白招惹?
一晃又过了几天,村子里风平浪静,什么事儿都没出。二叔松了一口气,暗暗庆幸自己沉得住气,没有吐露出别的。
事情就出在这天的上半夜。周家的小媳妇儿,爬起来给“大牲口棚”的牛、马添喂草料。她喂了一圈,独独不见家里那头健硕的水牛“老黑”。心头好生疑惑,这水牛能去哪里?又听得棚里隐约有些声响,便举着“煤油灯”细细看去。只见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水牛倒伏在角落,早没了气。大半边身子只剩下了森森白骨,一大团黑乎乎的的东西,将“老黑”紧紧裹住,还在不住的吞噬。周家小媳妇儿的那声尖叫:带着惶恐,带着愤怒,带着绝望。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几十年都过去了,原来谁也不曾忘却。
最先赶来的是周家的几个男人,他们看到了瘫倒在地上,崩溃的小媳妇儿。也看到了“牲口棚”里的可怕场景:那头水牛,只剩下小半段还有肉,大部分都成了骨架。但是吞噬水牛的东西,却没有了踪影。周家的人,脸都绿了,身子抖的厉害,就这么僵立着不动。村里人先后赶了过来,因为担心碰上了贼或者是野兽,不少男人手上还操着锄头、铁铲、木棒。
二叔也在人群当中,他的脸色苍白,如果不是手里握有一根木棒,都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等弄明白出了什么事,村民们面面相觑,一时没了主张,谁也不敢乱说话。
二叔大着胆子走进了“牲口棚”,举着“煤油灯”,里外又照了好一通。老周头看向他,紧张的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虎子,怎,怎么了?”二叔用木棒在地面戳了几下:“那东西,就藏在地里面”。
十几把锄头,铁铲在棚里挖了起来。挖了约摸半支烟的光景,村民们不再动手了,几十双眼睛,直勾勾 盯着翻挖出的泥土。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泥土上,沾染着大片大片鲜红的液体。村里的屠户用颤抖着的手沾了一点,只闻了闻,就变了脸色:“是牛血!”
二叔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睁开。他咬紧牙关,做了一个手势。村民们略略犹豫,便又挖了起来,约摸挖了十来分钟,村民们再次住了手。眼前的深坑里,有一大团鱼网状、深黑色的薄膜。如果完全铺展开来,那个面积怕是能覆盖住一头大象。二叔的头都大了,前后不过十来天,那玩意儿竟然生长得如此之大!
夜幕下,在村里的一处空旷所在,村民们牢牢地绑好了一口肥猪,估摸着也有二百多斤。屠户看准时机,在猪的喉咙上一刀刺入,伤口并不太深,那猪不断惨叫,鲜血汩汩地淌着。做好这一切,村民们各自寻好隐匿之处,埋伏起来静静的候着。
每个村民心中都忐忑不安,也不知等了多久,眼见得周围黑沉沉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鸟鸣。西北角的一株老树上,藏定一人,却是县里有名的老猎手。他伏在粗大的树干上,汗水自额头慢慢的渗出,他却一动也不动,只是用力紧握着那把猎枪。
二叔和老周家的,秉住了呼吸,各自蹲守在一口大水缸里。那大缸摆放在肥猪的两侧,双方相距不过两、三米远,每人手里都是一枝“五响翻子”。肥猪咽喉处的伤口越痛,便越挣扎。而肥猪越挣扎,血淌的便更多。不得不说,人是万物之灵。二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待那话儿现身,便打得它满身都是血窟窿眼。
蓦地,二叔只觉得脚下的大地,剧烈的抖动了起来。他小心翼翼的揭开缸盖,发现不远处鼓起了一个极大的土包,正一点一点的向肥猪的方向慢慢推进。他心里一紧,暗暗思量:终于等到你了!
土包的顶端,却在不停的蠕动着,分明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二叔长长的吐了口气,慢慢将手里的“五响翻子”对准了前方,手指因为紧张,微微有些发颤。他死命咬住下唇,都咬出血来了,这才稳住心神。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响,土包猛地翻了开来。二叔只瞧了一眼,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从缸里蹦出来。那土里冒出来的,竟然是成千上万只,又肥又大的灰毛老鼠!这老鼠群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便铺满了整个儿大地,疯狂的到处乱跑、乱钻。埋伏在四周的村民,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发一声喊,硬着头皮举起手中的锄头、铁铲奋力拍打。最奇的是,那些老鼠见了人,不但不怕,反而争先恐后的窜上身来,张口便咬。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眼见得数十个青壮年,人人身上都爬挂了无数只老鼠。村民们立刻乱了阵脚,有人实在撑不住了,撒开双腿,掉头往家中就跑。
树上的老猎人,对着躁动着的“鼠海”连连开了五、六枪,轰翻了一大片!但枪声、火药味儿,同类血肉模糊的尸体,受伤后翻滚挣扎的惨叫,一点儿也没有震慑到鼠群。老鼠们就像是疯了,完全是不管不顾的架式。二叔心里知道:完了!这混乱的局面,对村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他并不知道,这才刚刚拉开了序幕,真正的灭顶之灾还在后头呢。
二叔才窜出水缸,就遭到了几十只灰毛老鼠的疯狂撕咬,不到一分钟,身上就多处挂彩。他揩去脸上的血渍,飞快的打了声呼哨,一条黑狗便从不远处的灌木丛里窜出来。那黑狗体型巨大,好似牛犊大小,一看就知道非同寻常。二叔左手拍打着身上的老鼠,右手往鼠群一指,怒吼道:“老怪!给我狠狠的咬!”
黑狗的喉咙里发出炸雷似的声音,好不吓人!它准确的领会了主人的指令,从二叔身边一掠而过,箭一般迎着鼠群扑了上去。黑狗张开巨口,利如锋刃的狗牙横切竖割,草丛里,泥土里,黑狗的皮毛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攻击,鼠群起先是溃败的,但很快就开始了全面反击。黑狗即便再凶悍,面对成千上万的灰毛老鼠,也是绝无胜算!很快,狗血从浑身的十几个裂口中冒了出来,像是一条条小溪在无声的流淌。
但黑狗的战斗力是可怕的,竟然完全不在乎身上的伤势,仍在鼠群里左突右闯,前冲后撞,疯狂扑咬。这给了二叔一个机会。他跌跌撞撞,一头抢进了附近的一间“仓房”。那里摆放着木头、砖瓦、铁铲、锄头、马灯、煤油箱等杂物。他三两下扎好了一只“火把”,淋上了煤油,随手点燃,便冲了出来。
二叔咬牙切齿,手持“火把”,一步一步迎着鼠群走了过去。这一招极为有效,鼠群立时大乱。那老鼠见了火,如何不怕?纷纷退后,却不逃散,只围着“火把”团团打着转。二叔心里有数,胆子也更壮了,抢行几步,逼得鼠群又往后退了一段!口中大声喝道:“老周家的,叫上几个人,快去把村里的猫儿都赶过来!”
老周家的应了一声,撒腿就跑。在这乡下,家家几乎都养着猫儿避鼠的。天到这般时候,那些猫儿大多聚在一起,在茅屋外四下里游荡。二叔手中的“火把”此时虽旺,但鼠群似乎也明白,这火终会燃尽,并不远避。二叔心头焦躁,只盼着猫儿早些出来解困。忽见老周家的,抱着一只肥大的狸花猫,身后跟着五、六十个后生,每人怀里都抱着只猫儿,匆匆的赶了过来。
二叔心头,大喜过望。这猫和老鼠,是与生俱来的天敌。但凡是碰上了,必是要斗个不死不休。乡下的狸花猫,捕鼠更是能手。果然,那狸花猫看到老鼠,眼睛瞪得又大又圆。身上的毛倒竖起来,不待主人吩咐,喵的一声,便纵身一跃,扑了上去。这狸花猫实在是厉害,一口气便咬翻了数十只老鼠!那些个猫儿,见了老鼠,也都来了精神,一只接一只相继扑了上去,到处追咬。正在恶斗中的黑狗红了眼,它对身上的伤口已经麻木了。负了伤的黑狗没眨一下眼睛,就发动了新的进攻,必要置鼠群于死地。看准时机,黑狗发出一声声炸雷般的猛吼,化作黑色的旋风,朝前猛扑,又是一通死命撕咬。那鼠群虽说成千上万,但见了天敌,先自慌了。二叔和后生们,又先后点起了数十枝“火把”。鼠群再也扛不住了,四散奔逃,转眼间便逃得干干净净。
村民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过神来,看着满地血肉模糊的灰毛老鼠尸体,当真令人阵阵作呕,有些人更是张嘴吐了起来。二叔转脸,向那口肥猪的所在看去,不觉一怔,那头肥猪竟然不见了!二叔心里一慌,急忙奔到近前。方才只顾着和鼠群大战,地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大洞,黑洞洞的也不知深浅,那猪定是被拖入了洞穴深处。
二叔正犯着寻思,忽听得有人高喊道:“七爷,七爷怎么不见了?”那七爷便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一直藏身于西北角的老树上。好端端的,怎会不见了踪影?二叔找了一支手电,向下细细照去。赫然发现一只“长烟管”,正是七爷的心爱之物。想来,七爷定是看到肥猪被拖入了洞穴,他艺高人胆大,竟然也钻了进去。这时,有一些村民,也看出了情势不对,围了过来。
二叔把自己的推断,对众人简单的说了一下。便要带着黑狗下到洞穴,去接应七爷。众人哪肯让二叔一个人去犯险?当下选出来五、六个后生,人手一枝“五响翻子”,要陪着二叔一起探洞穴。
二叔打了个手势,黑狗便钻进了洞穴。二叔和那些后生,各自打着手电,紧紧地跟在黑狗的后面。那洞穴深处,却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虽然人人都拿着手电,也只不过能照亮前方两米的距离,再远的地方,那便是无尽的黑暗。
人在黑暗中行走,因为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心里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为防止发生意外,二叔特地又交代了一番。几个人在洞里走了几分钟后,大家的“方向感”就全没了。二叔倒不是太在意,只要有大黑狗在,这些都不算事儿。
走在队伍最后的,是一个叫大春的。他性子最是鲁莽,二叔怕他添乱,所以有意把他压在了队尾。说起来,大春是喝凉水塞牙缝,倒霉透了。在上个转弯处,他不小心崴脚了。按理来说,他应该立刻呼叫前面的队伍,但他为人过于好胜要强,暗暗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拖着右腿努力跟上。
又走了一段,大春的右腿脚踝处疼的越发厉害了。他用手电一照,自己也吓了一跳,那里肿的像是个馒头。他知道没法再跟下去,便对着前面大声喊着我二叔的名字:“虎子,虎子”。
二叔听见了,立刻摆手示意队伍停止前进,原地不动。大黑狗挺直了四腿,尾巴轻轻的晃了一下,在黑暗中的那双狗眼,闪闪发光。二叔拍了拍巨大的狗头,一个人向后找了过来。等两个人碰了面,二叔弄清了原委,又看了看大春的脚踝,耽搁不得。二叔当即决定,叫来一个后生,扶着大春原路返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后生搀扶着大春,打着手电慢慢的顺着来路往回走。才走了两个转弯口,大春就发现了问题,这路不对。周围实在是太黑了,两支手电筒照向远处,还是瞧得不太明白。大春黑着脸告诉后生:“我们方向走错了,这条路,我们压根没走过。”
后生是一脸懵逼。大春心里也觉得纳闷。这人下了洞穴,才走了多远?况且一路上,也没有看到有岔道啊。两人正犯着寻思,忽听得前方黑暗里,隐约传来几声狗吠。虽然听得不是很清,但大春和后生还是听出来了,是那只大黑狗发出的。
两人不禁呆了一呆。这是闹哪一出啊?怎么又绕到虎子那些人的前面来了?大春和后生想了想,还是打着手电,向着声音的方向摸了过去。
又走了好一段路,那狗吠声仍然是忽远忽近,飘忽不定,似是在引领着大春和后生。大春心里有些起疑,便站定了,不肯再往前去。后生的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安,在旁边悄声的说道:“大春哥,走了老半天了,那狗倒底在哪呢?要不,咱们喊两声试试?”
过了一会,大春轻声说道:“把手电都灭了”。后生微微一怔,随即照做了。四周顿时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大春又拉了拉后生的手,两人慢慢伏下身子。后生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这心跳得好厉害,和打鼓一般。
前面的黑暗处,又隐约传来了一些动静,但这次不是狗吠。大春慢慢用胳膊撞了撞身旁的后生,那人会意,两枝“五响翻子”同时顺过了枪管。又过了分把钟,只听得前面动静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仔细分辩,似乎是什么东西喘息的声音,好生的怪异。大春猛地打亮了手电,向前方照了过去。这手电的光亮并不好,但因为离的太近,大春和后生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大春那晚死在了当场,后生却侥幸活了下来,只是变成了疯子。后生一直到死,大伙儿在他嘴里,唯一听得明白的一句话是:“真的有鬼。”
走在最前面的大黑狗,忽然停了下来。摇晃着硕大的狗头,竖起了耳朵。不安的撮了撮鼻子,嗅着周围的空气,发出一阵粗闷的鼻息。二叔心里一紧,摸了摸那狗头。黑狗伸出舌头舔了舔二叔的手,不声不响地晃动着尾巴。二叔做了一个手势,大黑狗眦出了白森森的牙刀,伏低身子,慢慢地向前摸去。
转过弯来,大黑狗就在不远处,静静的卧着,无声的耸动着脸毛。二叔和三个伙伴,也随后赶了过来。几支手电照在了地上,大伙儿直瞧得脸色苍白,谁也作声不得。
地上扔着一把猎枪,那是县里有名儿的老猎人——七爷的心爱之物,枪身上却沾满了鲜血。二叔慢慢弯下腰,伸手去拾,那血,还没有全干!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句俗语:“枪在人在”的隐意。七爷如果还活着,断不会丢下这把猎枪。
二叔转脸问那几个同伴:“现在是回去,还是继续搜寻七爷?”一个后生鼓足了勇气,对二叔说:“虎子哥,七爷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他老人家都折在了这里,咱们还是先撤回去吧。”二叔知道这几个人是怕了,二叔自己心里也是有些发毛。
大黑狗却站了起来,暴躁地朝前跑了两步,又转回身来。前肢搭在二叔的身上,舔着二叔的手,轻轻的吠叫着。二叔想了想,还是跟着大黑狗向前走去。几个同伴略略迟疑,也都跟了上来。
约摸走了能有十来分钟,大黑狗再一次掉转过身来,绕着二叔兜起了圈子。洞穴里不通风,二叔等人提鼻子一闻,都不禁皱了皱眉头。前面传来的,是一股异味,熏得人一阵阵的作呕。几个人互相看了看,二叔冲他们摆了摆手,他一个人秉住这口气,悄悄的摸了过去。
手电照去,那是血肉模糊的一堆,有骨有肉。几个后生大着胆子摸了上来,看了一会儿,有人忍不住问道:“虎子哥,这会不会是?” 二叔“哼”了一声:“就是那头猪,这是被吃剩的。”话音未落,有人失声道:“那玩意儿,难道就在这附近?”
大黑狗突然纵身跳起,抖动着耳朵,发出阵阵低沉的吠叫。狗眼里冒出来兽性的凶狠,四条腿直直地挺立着,急促的摇摇尾巴,眦出如同刀锋一样锐利的牙齿。那牙齿,白生生的,在黑暗中看得格外的瘆人。二叔吸了口冷气,变了脸色:“那玩意儿就在这,咱们现在,怕是走不得了。”
大黑狗焦急地狂吠,蹬直了粗壮的后腿,随时准备扑过去。二叔将心一横,打了一声口哨。大黑狗一窜老远,直没入了黑暗里。二叔回过头看定几个同伴,脸上的表情有几分狰狞:“要走,你们只管走。我今天,要拼个鱼死网破”。
二叔一个人往前走去。他不用回头也知道,背后没有人跟上。他苦笑了一下,心头并不恨怨,反倒轻松了。生死有命,在此一搏。忽地,前面传来大黑狗,疯狂的吼叫声。大黑狗凶悍的战斗力,二叔是深知的。前年春天,村里闹开了狼,把村里的羊,先后拖走了四、五只。大黑狗被激怒了,不声不响地一路追踪,和狼群碰了个正着。最终大黑狗以一抵七,狗肚子被咬开,肠子都拖出来了,还是硬生生地咬死了七头饿狼。但现在面对的,是那个未知生物,大黑狗又有多少胜算呢?
据说人如果豁出去了一切,就不会畏惧死亡了。二叔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五响翻子”,直接冲了上去。



你们听说过哪些关于黄河的奇闻异事,历史故事?葭明通来说一段江苏徐州丰县废黄河变果园的历史故事吧!这个戈壁滩是怎么来的呢?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大沙河。起码应该有很多会读书懂科学的人来做这些工作才好!普通的农民群众是做不来这种工作的。然后就到了1957年!一致认为在“大沙河”应该直接种果树,尤其苹果树,不用搞什么防护林然后再造良田种庄稼的,不划算。遗惠今日!起码!在那个特殊年代,丰县征服了废黄河“小戈壁滩”,可以类比大寨梯田!
那是一个清晨,二叔去黄河边,取昨天晚上下好的网。让他意外的是,网里一条鱼也没有。却有一个透明的,乒乓球大小的物体。二叔有些好奇,用手指戳戳,感觉粘乎乎的。放在鼻子下面闻闻,有一股腥臭味,差点吐出来。
二叔很恼火,想把这个球状生物给扔了。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因为这个球状生物是活的,会扭来扭去。身体一会儿圆,一会儿扁,一会儿条。二叔看着有趣,就留了下来。
家中有个空置的水缸,二叔往里面倒了多半缸水,就把球状生物养在了里面。也许是怕太突兀了,还扔了五、六尾鲤鱼在里面。
二叔要忙去农活,一直到天擦黑,才回到了家里。想着早上捞的球状生物,便来到了水缸前。这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当真是吓了一跳。缸里的水,一片殷红。那生物倒还在缸里,只不过,已经变得有碗口那么大。缸里的五、六尾鲤鱼却只剩下了骨架,沉在了缸底。
二叔有些吃惊。这玩意儿,还能吃活鱼?他想了想,去厨下又捞了尾鲤鱼,投入了缸里。鲤鱼入缸,自由自在的游动着。没过多久,那个碗口大的生物,慢慢凑了过来,一下子便贴在了鲤鱼的身上。那鲤鱼拼命摆动,哪里挣脱的开?也就是眨眼睛的工夫,就被吞噬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缸里的水更是一片血红。
二叔倒抽了口冷气,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时,院里的长辈叫他去吃晚饭,他就暂时把这事儿给搁下了。等二叔再次想到这球状生物,已是第二天的晌午了。不知怎地,他心里有些发毛,人来到缸前,不禁又大吃一惊!
缸里只残留了一个篮球大小的透明膜儿,从中间撕裂了一个大洞,倒像是蜕下的皮。这玩意儿难道是跑了?二叔挠了挠头,在院里搜寻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也只好作罢了。
过了三、五天,二叔就把这事儿抛在了脑后。直到他有天傍晚收工回来,见邻居老王家门口,围了一大圈人。原来是老王媳妇儿站在门外“骂大街”,他才觉得是出了祸事!
老王家里,养了多年的一条黄狗。不吱声不吱气的,被吃得只剩下了骨架。老王媳妇儿那是一个泼辣女人,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这才站在自家门前破口大骂。二叔挤进了人群,看见了地上的黄狗骨架,打了个冷战。心头突突的乱跳,张嘴想说些什么,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二叔低着头,进了家门,他的心里很乱。第一,他不能确定,吃掉黄狗的,就是那个玩意儿。第二,就算说出来了,村里会有人信吗?第三,那玩意儿是他带回村里的,吃了一条黄狗事小,那老王媳妇儿却是出了名的泼辣货,二叔怎敢平白招惹?
一晃又过了几天,村子里风平浪静,什么事儿都没出。二叔松了一口气,暗暗庆幸自己沉得住气,没有吐露出别的。
事情就出在这天的上半夜。周家的小媳妇儿,爬起来给“大牲口棚”的牛、马添喂草料。她喂了一圈,独独不见家里那头健硕的水牛“老黑”。心头好生疑惑,这水牛能去哪里?又听得棚里隐约有些声响,便举着“煤油灯”细细看去。只见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水牛倒伏在角落,早没了气。大半边身子只剩下了森森白骨,一大团黑乎乎的的东西,将“老黑”紧紧裹住,还在不住的吞噬。周家小媳妇儿的那声尖叫:带着惶恐,带着愤怒,带着绝望。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几十年都过去了,原来谁也不曾忘却。
最先赶来的是周家的几个男人,他们看到了瘫倒在地上,崩溃的小媳妇儿。也看到了“牲口棚”里的可怕场景:那头水牛,只剩下小半段还有肉,大部分都成了骨架。但是吞噬水牛的东西,却没有了踪影。周家的人,脸都绿了,身子抖的厉害,就这么僵立着不动。村里人先后赶了过来,因为担心碰上了贼或者是野兽,不少男人手上还操着锄头、铁铲、木棒。
二叔也在人群当中,他的脸色苍白,如果不是手里握有一根木棒,都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等弄明白出了什么事,村民们面面相觑,一时没了主张,谁也不敢乱说话。
二叔大着胆子走进了“牲口棚”,举着“煤油灯”,里外又照了好一通。老周头看向他,紧张的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虎子,怎,怎么了?”二叔用木棒在地面戳了几下:“那东西,就藏在地里面”。
十几把锄头,铁铲在棚里挖了起来。挖了约摸半支烟的光景,村民们不再动手了,几十双眼睛,直勾勾 盯着翻挖出的泥土。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泥土上,沾染着大片大片鲜红的液体。村里的屠户用颤抖着的手沾了一点,只闻了闻,就变了脸色:“是牛血!”
二叔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睁开。他咬紧牙关,做了一个手势。村民们略略犹豫,便又挖了起来,约摸挖了十来分钟,村民们再次住了手。眼前的深坑里,有一大团鱼网状、深黑色的薄膜。如果完全铺展开来,那个面积怕是能覆盖住一头大象。二叔的头都大了,前后不过十来天,那玩意儿竟然生长得如此之大!
夜幕下,在村里的一处空旷所在,村民们牢牢地绑好了一口肥猪,估摸着也有二百多斤。屠户看准时机,在猪的喉咙上一刀刺入,伤口并不太深,那猪不断惨叫,鲜血汩汩地淌着。做好这一切,村民们各自寻好隐匿之处,埋伏起来静静的候着。
每个村民心中都忐忑不安,也不知等了多久,眼见得周围黑沉沉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鸟鸣。西北角的一株老树上,藏定一人,却是县里有名的老猎手。他伏在粗大的树干上,汗水自额头慢慢的渗出,他却一动也不动,只是用力紧握着那把猎枪。
二叔和老周家的,秉住了呼吸,各自蹲守在一口大水缸里。那大缸摆放在肥猪的两侧,双方相距不过两、三米远,每人手里都是一枝“五响翻子”。肥猪咽喉处的伤口越痛,便越挣扎。而肥猪越挣扎,血淌的便更多。不得不说,人是万物之灵。二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待那话儿现身,便打得它满身都是血窟窿眼。
蓦地,二叔只觉得脚下的大地,剧烈的抖动了起来。他小心翼翼的揭开缸盖,发现不远处鼓起了一个极大的土包,正一点一点的向肥猪的方向慢慢推进。他心里一紧,暗暗思量:终于等到你了!
土包的顶端,却在不停的蠕动着,分明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二叔长长的吐了口气,慢慢将手里的“五响翻子”对准了前方,手指因为紧张,微微有些发颤。他死命咬住下唇,都咬出血来了,这才稳住心神。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响,土包猛地翻了开来。二叔只瞧了一眼,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从缸里蹦出来。那土里冒出来的,竟然是成千上万只,又肥又大的灰毛老鼠!这老鼠群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便铺满了整个儿大地,疯狂的到处乱跑、乱钻。埋伏在四周的村民,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发一声喊,硬着头皮举起手中的锄头、铁铲奋力拍打。最奇的是,那些老鼠见了人,不但不怕,反而争先恐后的窜上身来,张口便咬。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眼见得数十个青壮年,人人身上都爬挂了无数只老鼠。村民们立刻乱了阵脚,有人实在撑不住了,撒开双腿,掉头往家中就跑。
树上的老猎人,对着躁动着的“鼠海”连连开了五、六枪,轰翻了一大片!但枪声、火药味儿,同类血肉模糊的尸体,受伤后翻滚挣扎的惨叫,一点儿也没有震慑到鼠群。老鼠们就像是疯了,完全是不管不顾的架式。二叔心里知道:完了!这混乱的局面,对村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他并不知道,这才刚刚拉开了序幕,真正的灭顶之灾还在后头呢。
二叔才窜出水缸,就遭到了几十只灰毛老鼠的疯狂撕咬,不到一分钟,身上就多处挂彩。他揩去脸上的血渍,飞快的打了声呼哨,一条黑狗便从不远处的灌木丛里窜出来。那黑狗体型巨大,好似牛犊大小,一看就知道非同寻常。二叔左手拍打着身上的老鼠,右手往鼠群一指,怒吼道:“老怪!给我狠狠的咬!”
黑狗的喉咙里发出炸雷似的声音,好不吓人!它准确的领会了主人的指令,从二叔身边一掠而过,箭一般迎着鼠群扑了上去。黑狗张开巨口,利如锋刃的狗牙横切竖割,草丛里,泥土里,黑狗的皮毛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攻击,鼠群起先是溃败的,但很快就开始了全面反击。黑狗即便再凶悍,面对成千上万的灰毛老鼠,也是绝无胜算!很快,狗血从浑身的十几个裂口中冒了出来,像是一条条小溪在无声的流淌。
但黑狗的战斗力是可怕的,竟然完全不在乎身上的伤势,仍在鼠群里左突右闯,前冲后撞,疯狂扑咬。这给了二叔一个机会。他跌跌撞撞,一头抢进了附近的一间“仓房”。那里摆放着木头、砖瓦、铁铲、锄头、马灯、煤油箱等杂物。他三两下扎好了一只“火把”,淋上了煤油,随手点燃,便冲了出来。
二叔咬牙切齿,手持“火把”,一步一步迎着鼠群走了过去。这一招极为有效,鼠群立时大乱。那老鼠见了火,如何不怕?纷纷退后,却不逃散,只围着“火把”团团打着转。二叔心里有数,胆子也更壮了,抢行几步,逼得鼠群又往后退了一段!口中大声喝道:“老周家的,叫上几个人,快去把村里的猫儿都赶过来!”
老周家的应了一声,撒腿就跑。在这乡下,家家几乎都养着猫儿避鼠的。天到这般时候,那些猫儿大多聚在一起,在茅屋外四下里游荡。二叔手中的“火把”此时虽旺,但鼠群似乎也明白,这火终会燃尽,并不远避。二叔心头焦躁,只盼着猫儿早些出来解困。忽见老周家的,抱着一只肥大的狸花猫,身后跟着五、六十个后生,每人怀里都抱着只猫儿,匆匆的赶了过来。
二叔心头,大喜过望。这猫和老鼠,是与生俱来的天敌。但凡是碰上了,必是要斗个不死不休。乡下的狸花猫,捕鼠更是能手。果然,那狸花猫看到老鼠,眼睛瞪得又大又圆。身上的毛倒竖起来,不待主人吩咐,喵的一声,便纵身一跃,扑了上去。这狸花猫实在是厉害,一口气便咬翻了数十只老鼠!那些个猫儿,见了老鼠,也都来了精神,一只接一只相继扑了上去,到处追咬。正在恶斗中的黑狗红了眼,它对身上的伤口已经麻木了。负了伤的黑狗没眨一下眼睛,就发动了新的进攻,必要置鼠群于死地。看准时机,黑狗发出一声声炸雷般的猛吼,化作黑色的旋风,朝前猛扑,又是一通死命撕咬。那鼠群虽说成千上万,但见了天敌,先自慌了。二叔和后生们,又先后点起了数十枝“火把”。鼠群再也扛不住了,四散奔逃,转眼间便逃得干干净净。
村民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过神来,看着满地血肉模糊的灰毛老鼠尸体,当真令人阵阵作呕,有些人更是张嘴吐了起来。二叔转脸,向那口肥猪的所在看去,不觉一怔,那头肥猪竟然不见了!二叔心里一慌,急忙奔到近前。方才只顾着和鼠群大战,地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大洞,黑洞洞的也不知深浅,那猪定是被拖入了洞穴深处。
二叔正犯着寻思,忽听得有人高喊道:“七爷,七爷怎么不见了?”那七爷便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一直藏身于西北角的老树上。好端端的,怎会不见了踪影?二叔找了一支手电,向下细细照去。赫然发现一只“长烟管”,正是七爷的心爱之物。想来,七爷定是看到肥猪被拖入了洞穴,他艺高人胆大,竟然也钻了进去。这时,有一些村民,也看出了情势不对,围了过来。
二叔把自己的推断,对众人简单的说了一下。便要带着黑狗下到洞穴,去接应七爷。众人哪肯让二叔一个人去犯险?当下选出来五、六个后生,人手一枝“五响翻子”,要陪着二叔一起探洞穴。
二叔打了个手势,黑狗便钻进了洞穴。二叔和那些后生,各自打着手电,紧紧地跟在黑狗的后面。那洞穴深处,却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虽然人人都拿着手电,也只不过能照亮前方两米的距离,再远的地方,那便是无尽的黑暗。
人在黑暗中行走,因为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心里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为防止发生意外,二叔特地又交代了一番。几个人在洞里走了几分钟后,大家的“方向感”就全没了。二叔倒不是太在意,只要有大黑狗在,这些都不算事儿。
走在队伍最后的,是一个叫大春的。他性子最是鲁莽,二叔怕他添乱,所以有意把他压在了队尾。说起来,大春是喝凉水塞牙缝,倒霉透了。在上个转弯处,他不小心崴脚了。按理来说,他应该立刻呼叫前面的队伍,但他为人过于好胜要强,暗暗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拖着右腿努力跟上。
又走了一段,大春的右腿脚踝处疼的越发厉害了。他用手电一照,自己也吓了一跳,那里肿的像是个馒头。他知道没法再跟下去,便对着前面大声喊着我二叔的名字:“虎子,虎子”。
二叔听见了,立刻摆手示意队伍停止前进,原地不动。大黑狗挺直了四腿,尾巴轻轻的晃了一下,在黑暗中的那双狗眼,闪闪发光。二叔拍了拍巨大的狗头,一个人向后找了过来。等两个人碰了面,二叔弄清了原委,又看了看大春的脚踝,耽搁不得。二叔当即决定,叫来一个后生,扶着大春原路返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后生搀扶着大春,打着手电慢慢的顺着来路往回走。才走了两个转弯口,大春就发现了问题,这路不对。周围实在是太黑了,两支手电筒照向远处,还是瞧得不太明白。大春黑着脸告诉后生:“我们方向走错了,这条路,我们压根没走过。”
后生是一脸懵逼。大春心里也觉得纳闷。这人下了洞穴,才走了多远?况且一路上,也没有看到有岔道啊。两人正犯着寻思,忽听得前方黑暗里,隐约传来几声狗吠。虽然听得不是很清,但大春和后生还是听出来了,是那只大黑狗发出的。
两人不禁呆了一呆。这是闹哪一出啊?怎么又绕到虎子那些人的前面来了?大春和后生想了想,还是打着手电,向着声音的方向摸了过去。
又走了好一段路,那狗吠声仍然是忽远忽近,飘忽不定,似是在引领着大春和后生。大春心里有些起疑,便站定了,不肯再往前去。后生的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安,在旁边悄声的说道:“大春哥,走了老半天了,那狗倒底在哪呢?要不,咱们喊两声试试?”
过了一会,大春轻声说道:“把手电都灭了”。后生微微一怔,随即照做了。四周顿时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大春又拉了拉后生的手,两人慢慢伏下身子。后生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这心跳得好厉害,和打鼓一般。
前面的黑暗处,又隐约传来了一些动静,但这次不是狗吠。大春慢慢用胳膊撞了撞身旁的后生,那人会意,两枝“五响翻子”同时顺过了枪管。又过了分把钟,只听得前面动静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仔细分辩,似乎是什么东西喘息的声音,好生的怪异。大春猛地打亮了手电,向前方照了过去。这手电的光亮并不好,但因为离的太近,大春和后生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大春那晚死在了当场,后生却侥幸活了下来,只是变成了疯子。后生一直到死,大伙儿在他嘴里,唯一听得明白的一句话是:“真的有鬼。”
走在最前面的大黑狗,忽然停了下来。摇晃着硕大的狗头,竖起了耳朵。不安的撮了撮鼻子,嗅着周围的空气,发出一阵粗闷的鼻息。二叔心里一紧,摸了摸那狗头。黑狗伸出舌头舔了舔二叔的手,不声不响地晃动着尾巴。二叔做了一个手势,大黑狗眦出了白森森的牙刀,伏低身子,慢慢地向前摸去。
转过弯来,大黑狗就在不远处,静静的卧着,无声的耸动着脸毛。二叔和三个伙伴,也随后赶了过来。几支手电照在了地上,大伙儿直瞧得脸色苍白,谁也作声不得。
地上扔着一把猎枪,那是县里有名儿的老猎人——七爷的心爱之物,枪身上却沾满了鲜血。二叔慢慢弯下腰,伸手去拾,那血,还没有全干!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句俗语:“枪在人在”的隐意。七爷如果还活着,断不会丢下这把猎枪。
二叔转脸问那几个同伴:“现在是回去,还是继续搜寻七爷?”一个后生鼓足了勇气,对二叔说:“虎子哥,七爷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他老人家都折在了这里,咱们还是先撤回去吧。”二叔知道这几个人是怕了,二叔自己心里也是有些发毛。
大黑狗却站了起来,暴躁地朝前跑了两步,又转回身来。前肢搭在二叔的身上,舔着二叔的手,轻轻的吠叫着。二叔想了想,还是跟着大黑狗向前走去。几个同伴略略迟疑,也都跟了上来。
约摸走了能有十来分钟,大黑狗再一次掉转过身来,绕着二叔兜起了圈子。洞穴里不通风,二叔等人提鼻子一闻,都不禁皱了皱眉头。前面传来的,是一股异味,熏得人一阵阵的作呕。几个人互相看了看,二叔冲他们摆了摆手,他一个人秉住这口气,悄悄的摸了过去。
手电照去,那是血肉模糊的一堆,有骨有肉。几个后生大着胆子摸了上来,看了一会儿,有人忍不住问道:“虎子哥,这会不会是?” 二叔“哼”了一声:“就是那头猪,这是被吃剩的。”话音未落,有人失声道:“那玩意儿,难道就在这附近?”
大黑狗突然纵身跳起,抖动着耳朵,发出阵阵低沉的吠叫。狗眼里冒出来兽性的凶狠,四条腿直直地挺立着,急促的摇摇尾巴,眦出如同刀锋一样锐利的牙齿。那牙齿,白生生的,在黑暗中看得格外的瘆人。二叔吸了口冷气,变了脸色:“那玩意儿就在这,咱们现在,怕是走不得了。”
大黑狗焦急地狂吠,蹬直了粗壮的后腿,随时准备扑过去。二叔将心一横,打了一声口哨。大黑狗一窜老远,直没入了黑暗里。二叔回过头看定几个同伴,脸上的表情有几分狰狞:“要走,你们只管走。我今天,要拼个鱼死网破”。
二叔一个人往前走去。他不用回头也知道,背后没有人跟上。他苦笑了一下,心头并不恨怨,反倒轻松了。生死有命,在此一搏。忽地,前面传来大黑狗,疯狂的吼叫声。大黑狗凶悍的战斗力,二叔是深知的。前年春天,村里闹开了狼,把村里的羊,先后拖走了四、五只。大黑狗被激怒了,不声不响地一路追踪,和狼群碰了个正着。最终大黑狗以一抵七,狗肚子被咬开,肠子都拖出来了,还是硬生生地咬死了七头饿狼。但现在面对的,是那个未知生物,大黑狗又有多少胜算呢?
据说人如果豁出去了一切,就不会畏惧死亡了。二叔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五响翻子”,直接冲了上去。



你们听说过哪些关于黄河的奇闻异事,历史故事?葭明通来说一段江苏徐州丰县废黄河变果园的历史故事吧!这个戈壁滩是怎么来的呢?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大沙河。起码应该有很多会读书懂科学的人来做这些工作才好!普通的农民群众是做不来这种工作的。然后就到了1957年!一致认为在“大沙河”应该直接种果树,尤其苹果树,不用搞什么防护林然后再造良田种庄稼的,不划算。遗惠今日!起码!在那个特殊年代,丰县征服了废黄河“小戈壁滩”,可以类比大寨梯田!
那是一个清晨,二叔去黄河边,取昨天晚上下好的网。让他意外的是,网里一条鱼也没有。却有一个透明的,乒乓球大小的物体。二叔有些好奇,用手指戳戳,感觉粘乎乎的。放在鼻子下面闻闻,有一股腥臭味,差点吐出来。
二叔很恼火,想把这个球状生物给扔了。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因为这个球状生物是活的,会扭来扭去。身体一会儿圆,一会儿扁,一会儿条。二叔看着有趣,就留了下来。
家中有个空置的水缸,二叔往里面倒了多半缸水,就把球状生物养在了里面。也许是怕太突兀了,还扔了五、六尾鲤鱼在里面。
二叔要忙去农活,一直到天擦黑,才回到了家里。想着早上捞的球状生物,便来到了水缸前。这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当真是吓了一跳。缸里的水,一片殷红。那生物倒还在缸里,只不过,已经变得有碗口那么大。缸里的五、六尾鲤鱼却只剩下了骨架,沉在了缸底。
二叔有些吃惊。这玩意儿,还能吃活鱼?他想了想,去厨下又捞了尾鲤鱼,投入了缸里。鲤鱼入缸,自由自在的游动着。没过多久,那个碗口大的生物,慢慢凑了过来,一下子便贴在了鲤鱼的身上。那鲤鱼拼命摆动,哪里挣脱的开?也就是眨眼睛的工夫,就被吞噬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缸里的水更是一片血红。
二叔倒抽了口冷气,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时,院里的长辈叫他去吃晚饭,他就暂时把这事儿给搁下了。等二叔再次想到这球状生物,已是第二天的晌午了。不知怎地,他心里有些发毛,人来到缸前,不禁又大吃一惊!
缸里只残留了一个篮球大小的透明膜儿,从中间撕裂了一个大洞,倒像是蜕下的皮。这玩意儿难道是跑了?二叔挠了挠头,在院里搜寻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也只好作罢了。
过了三、五天,二叔就把这事儿抛在了脑后。直到他有天傍晚收工回来,见邻居老王家门口,围了一大圈人。原来是老王媳妇儿站在门外“骂大街”,他才觉得是出了祸事!
老王家里,养了多年的一条黄狗。不吱声不吱气的,被吃得只剩下了骨架。老王媳妇儿那是一个泼辣女人,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这才站在自家门前破口大骂。二叔挤进了人群,看见了地上的黄狗骨架,打了个冷战。心头突突的乱跳,张嘴想说些什么,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二叔低着头,进了家门,他的心里很乱。第一,他不能确定,吃掉黄狗的,就是那个玩意儿。第二,就算说出来了,村里会有人信吗?第三,那玩意儿是他带回村里的,吃了一条黄狗事小,那老王媳妇儿却是出了名的泼辣货,二叔怎敢平白招惹?
一晃又过了几天,村子里风平浪静,什么事儿都没出。二叔松了一口气,暗暗庆幸自己沉得住气,没有吐露出别的。
事情就出在这天的上半夜。周家的小媳妇儿,爬起来给“大牲口棚”的牛、马添喂草料。她喂了一圈,独独不见家里那头健硕的水牛“老黑”。心头好生疑惑,这水牛能去哪里?又听得棚里隐约有些声响,便举着“煤油灯”细细看去。只见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水牛倒伏在角落,早没了气。大半边身子只剩下了森森白骨,一大团黑乎乎的的东西,将“老黑”紧紧裹住,还在不住的吞噬。周家小媳妇儿的那声尖叫:带着惶恐,带着愤怒,带着绝望。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几十年都过去了,原来谁也不曾忘却。
最先赶来的是周家的几个男人,他们看到了瘫倒在地上,崩溃的小媳妇儿。也看到了“牲口棚”里的可怕场景:那头水牛,只剩下小半段还有肉,大部分都成了骨架。但是吞噬水牛的东西,却没有了踪影。周家的人,脸都绿了,身子抖的厉害,就这么僵立着不动。村里人先后赶了过来,因为担心碰上了贼或者是野兽,不少男人手上还操着锄头、铁铲、木棒。
二叔也在人群当中,他的脸色苍白,如果不是手里握有一根木棒,都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等弄明白出了什么事,村民们面面相觑,一时没了主张,谁也不敢乱说话。
二叔大着胆子走进了“牲口棚”,举着“煤油灯”,里外又照了好一通。老周头看向他,紧张的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虎子,怎,怎么了?”二叔用木棒在地面戳了几下:“那东西,就藏在地里面”。
十几把锄头,铁铲在棚里挖了起来。挖了约摸半支烟的光景,村民们不再动手了,几十双眼睛,直勾勾 盯着翻挖出的泥土。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泥土上,沾染着大片大片鲜红的液体。村里的屠户用颤抖着的手沾了一点,只闻了闻,就变了脸色:“是牛血!”
二叔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睁开。他咬紧牙关,做了一个手势。村民们略略犹豫,便又挖了起来,约摸挖了十来分钟,村民们再次住了手。眼前的深坑里,有一大团鱼网状、深黑色的薄膜。如果完全铺展开来,那个面积怕是能覆盖住一头大象。二叔的头都大了,前后不过十来天,那玩意儿竟然生长得如此之大!
夜幕下,在村里的一处空旷所在,村民们牢牢地绑好了一口肥猪,估摸着也有二百多斤。屠户看准时机,在猪的喉咙上一刀刺入,伤口并不太深,那猪不断惨叫,鲜血汩汩地淌着。做好这一切,村民们各自寻好隐匿之处,埋伏起来静静的候着。
每个村民心中都忐忑不安,也不知等了多久,眼见得周围黑沉沉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鸟鸣。西北角的一株老树上,藏定一人,却是县里有名的老猎手。他伏在粗大的树干上,汗水自额头慢慢的渗出,他却一动也不动,只是用力紧握着那把猎枪。
二叔和老周家的,秉住了呼吸,各自蹲守在一口大水缸里。那大缸摆放在肥猪的两侧,双方相距不过两、三米远,每人手里都是一枝“五响翻子”。肥猪咽喉处的伤口越痛,便越挣扎。而肥猪越挣扎,血淌的便更多。不得不说,人是万物之灵。二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待那话儿现身,便打得它满身都是血窟窿眼。
蓦地,二叔只觉得脚下的大地,剧烈的抖动了起来。他小心翼翼的揭开缸盖,发现不远处鼓起了一个极大的土包,正一点一点的向肥猪的方向慢慢推进。他心里一紧,暗暗思量:终于等到你了!
土包的顶端,却在不停的蠕动着,分明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二叔长长的吐了口气,慢慢将手里的“五响翻子”对准了前方,手指因为紧张,微微有些发颤。他死命咬住下唇,都咬出血来了,这才稳住心神。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响,土包猛地翻了开来。二叔只瞧了一眼,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从缸里蹦出来。那土里冒出来的,竟然是成千上万只,又肥又大的灰毛老鼠!这老鼠群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便铺满了整个儿大地,疯狂的到处乱跑、乱钻。埋伏在四周的村民,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发一声喊,硬着头皮举起手中的锄头、铁铲奋力拍打。最奇的是,那些老鼠见了人,不但不怕,反而争先恐后的窜上身来,张口便咬。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眼见得数十个青壮年,人人身上都爬挂了无数只老鼠。村民们立刻乱了阵脚,有人实在撑不住了,撒开双腿,掉头往家中就跑。
树上的老猎人,对着躁动着的“鼠海”连连开了五、六枪,轰翻了一大片!但枪声、火药味儿,同类血肉模糊的尸体,受伤后翻滚挣扎的惨叫,一点儿也没有震慑到鼠群。老鼠们就像是疯了,完全是不管不顾的架式。二叔心里知道:完了!这混乱的局面,对村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他并不知道,这才刚刚拉开了序幕,真正的灭顶之灾还在后头呢。
二叔才窜出水缸,就遭到了几十只灰毛老鼠的疯狂撕咬,不到一分钟,身上就多处挂彩。他揩去脸上的血渍,飞快的打了声呼哨,一条黑狗便从不远处的灌木丛里窜出来。那黑狗体型巨大,好似牛犊大小,一看就知道非同寻常。二叔左手拍打着身上的老鼠,右手往鼠群一指,怒吼道:“老怪!给我狠狠的咬!”
黑狗的喉咙里发出炸雷似的声音,好不吓人!它准确的领会了主人的指令,从二叔身边一掠而过,箭一般迎着鼠群扑了上去。黑狗张开巨口,利如锋刃的狗牙横切竖割,草丛里,泥土里,黑狗的皮毛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攻击,鼠群起先是溃败的,但很快就开始了全面反击。黑狗即便再凶悍,面对成千上万的灰毛老鼠,也是绝无胜算!很快,狗血从浑身的十几个裂口中冒了出来,像是一条条小溪在无声的流淌。
但黑狗的战斗力是可怕的,竟然完全不在乎身上的伤势,仍在鼠群里左突右闯,前冲后撞,疯狂扑咬。这给了二叔一个机会。他跌跌撞撞,一头抢进了附近的一间“仓房”。那里摆放着木头、砖瓦、铁铲、锄头、马灯、煤油箱等杂物。他三两下扎好了一只“火把”,淋上了煤油,随手点燃,便冲了出来。
二叔咬牙切齿,手持“火把”,一步一步迎着鼠群走了过去。这一招极为有效,鼠群立时大乱。那老鼠见了火,如何不怕?纷纷退后,却不逃散,只围着“火把”团团打着转。二叔心里有数,胆子也更壮了,抢行几步,逼得鼠群又往后退了一段!口中大声喝道:“老周家的,叫上几个人,快去把村里的猫儿都赶过来!”
老周家的应了一声,撒腿就跑。在这乡下,家家几乎都养着猫儿避鼠的。天到这般时候,那些猫儿大多聚在一起,在茅屋外四下里游荡。二叔手中的“火把”此时虽旺,但鼠群似乎也明白,这火终会燃尽,并不远避。二叔心头焦躁,只盼着猫儿早些出来解困。忽见老周家的,抱着一只肥大的狸花猫,身后跟着五、六十个后生,每人怀里都抱着只猫儿,匆匆的赶了过来。
二叔心头,大喜过望。这猫和老鼠,是与生俱来的天敌。但凡是碰上了,必是要斗个不死不休。乡下的狸花猫,捕鼠更是能手。果然,那狸花猫看到老鼠,眼睛瞪得又大又圆。身上的毛倒竖起来,不待主人吩咐,喵的一声,便纵身一跃,扑了上去。这狸花猫实在是厉害,一口气便咬翻了数十只老鼠!那些个猫儿,见了老鼠,也都来了精神,一只接一只相继扑了上去,到处追咬。正在恶斗中的黑狗红了眼,它对身上的伤口已经麻木了。负了伤的黑狗没眨一下眼睛,就发动了新的进攻,必要置鼠群于死地。看准时机,黑狗发出一声声炸雷般的猛吼,化作黑色的旋风,朝前猛扑,又是一通死命撕咬。那鼠群虽说成千上万,但见了天敌,先自慌了。二叔和后生们,又先后点起了数十枝“火把”。鼠群再也扛不住了,四散奔逃,转眼间便逃得干干净净。
村民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过神来,看着满地血肉模糊的灰毛老鼠尸体,当真令人阵阵作呕,有些人更是张嘴吐了起来。二叔转脸,向那口肥猪的所在看去,不觉一怔,那头肥猪竟然不见了!二叔心里一慌,急忙奔到近前。方才只顾着和鼠群大战,地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大洞,黑洞洞的也不知深浅,那猪定是被拖入了洞穴深处。
二叔正犯着寻思,忽听得有人高喊道:“七爷,七爷怎么不见了?”那七爷便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一直藏身于西北角的老树上。好端端的,怎会不见了踪影?二叔找了一支手电,向下细细照去。赫然发现一只“长烟管”,正是七爷的心爱之物。想来,七爷定是看到肥猪被拖入了洞穴,他艺高人胆大,竟然也钻了进去。这时,有一些村民,也看出了情势不对,围了过来。
二叔把自己的推断,对众人简单的说了一下。便要带着黑狗下到洞穴,去接应七爷。众人哪肯让二叔一个人去犯险?当下选出来五、六个后生,人手一枝“五响翻子”,要陪着二叔一起探洞穴。
二叔打了个手势,黑狗便钻进了洞穴。二叔和那些后生,各自打着手电,紧紧地跟在黑狗的后面。那洞穴深处,却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虽然人人都拿着手电,也只不过能照亮前方两米的距离,再远的地方,那便是无尽的黑暗。
人在黑暗中行走,因为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心里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为防止发生意外,二叔特地又交代了一番。几个人在洞里走了几分钟后,大家的“方向感”就全没了。二叔倒不是太在意,只要有大黑狗在,这些都不算事儿。
走在队伍最后的,是一个叫大春的。他性子最是鲁莽,二叔怕他添乱,所以有意把他压在了队尾。说起来,大春是喝凉水塞牙缝,倒霉透了。在上个转弯处,他不小心崴脚了。按理来说,他应该立刻呼叫前面的队伍,但他为人过于好胜要强,暗暗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拖着右腿努力跟上。
又走了一段,大春的右腿脚踝处疼的越发厉害了。他用手电一照,自己也吓了一跳,那里肿的像是个馒头。他知道没法再跟下去,便对着前面大声喊着我二叔的名字:“虎子,虎子”。
二叔听见了,立刻摆手示意队伍停止前进,原地不动。大黑狗挺直了四腿,尾巴轻轻的晃了一下,在黑暗中的那双狗眼,闪闪发光。二叔拍了拍巨大的狗头,一个人向后找了过来。等两个人碰了面,二叔弄清了原委,又看了看大春的脚踝,耽搁不得。二叔当即决定,叫来一个后生,扶着大春原路返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后生搀扶着大春,打着手电慢慢的顺着来路往回走。才走了两个转弯口,大春就发现了问题,这路不对。周围实在是太黑了,两支手电筒照向远处,还是瞧得不太明白。大春黑着脸告诉后生:“我们方向走错了,这条路,我们压根没走过。”
后生是一脸懵逼。大春心里也觉得纳闷。这人下了洞穴,才走了多远?况且一路上,也没有看到有岔道啊。两人正犯着寻思,忽听得前方黑暗里,隐约传来几声狗吠。虽然听得不是很清,但大春和后生还是听出来了,是那只大黑狗发出的。
两人不禁呆了一呆。这是闹哪一出啊?怎么又绕到虎子那些人的前面来了?大春和后生想了想,还是打着手电,向着声音的方向摸了过去。
又走了好一段路,那狗吠声仍然是忽远忽近,飘忽不定,似是在引领着大春和后生。大春心里有些起疑,便站定了,不肯再往前去。后生的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安,在旁边悄声的说道:“大春哥,走了老半天了,那狗倒底在哪呢?要不,咱们喊两声试试?”
过了一会,大春轻声说道:“把手电都灭了”。后生微微一怔,随即照做了。四周顿时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大春又拉了拉后生的手,两人慢慢伏下身子。后生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这心跳得好厉害,和打鼓一般。
前面的黑暗处,又隐约传来了一些动静,但这次不是狗吠。大春慢慢用胳膊撞了撞身旁的后生,那人会意,两枝“五响翻子”同时顺过了枪管。又过了分把钟,只听得前面动静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仔细分辩,似乎是什么东西喘息的声音,好生的怪异。大春猛地打亮了手电,向前方照了过去。这手电的光亮并不好,但因为离的太近,大春和后生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大春那晚死在了当场,后生却侥幸活了下来,只是变成了疯子。后生一直到死,大伙儿在他嘴里,唯一听得明白的一句话是:“真的有鬼。”
走在最前面的大黑狗,忽然停了下来。摇晃着硕大的狗头,竖起了耳朵。不安的撮了撮鼻子,嗅着周围的空气,发出一阵粗闷的鼻息。二叔心里一紧,摸了摸那狗头。黑狗伸出舌头舔了舔二叔的手,不声不响地晃动着尾巴。二叔做了一个手势,大黑狗眦出了白森森的牙刀,伏低身子,慢慢地向前摸去。
转过弯来,大黑狗就在不远处,静静的卧着,无声的耸动着脸毛。二叔和三个伙伴,也随后赶了过来。几支手电照在了地上,大伙儿直瞧得脸色苍白,谁也作声不得。
地上扔着一把猎枪,那是县里有名儿的老猎人——七爷的心爱之物,枪身上却沾满了鲜血。二叔慢慢弯下腰,伸手去拾,那血,还没有全干!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句俗语:“枪在人在”的隐意。七爷如果还活着,断不会丢下这把猎枪。
二叔转脸问那几个同伴:“现在是回去,还是继续搜寻七爷?”一个后生鼓足了勇气,对二叔说:“虎子哥,七爷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他老人家都折在了这里,咱们还是先撤回去吧。”二叔知道这几个人是怕了,二叔自己心里也是有些发毛。
大黑狗却站了起来,暴躁地朝前跑了两步,又转回身来。前肢搭在二叔的身上,舔着二叔的手,轻轻的吠叫着。二叔想了想,还是跟着大黑狗向前走去。几个同伴略略迟疑,也都跟了上来。
约摸走了能有十来分钟,大黑狗再一次掉转过身来,绕着二叔兜起了圈子。洞穴里不通风,二叔等人提鼻子一闻,都不禁皱了皱眉头。前面传来的,是一股异味,熏得人一阵阵的作呕。几个人互相看了看,二叔冲他们摆了摆手,他一个人秉住这口气,悄悄的摸了过去。
手电照去,那是血肉模糊的一堆,有骨有肉。几个后生大着胆子摸了上来,看了一会儿,有人忍不住问道:“虎子哥,这会不会是?” 二叔“哼”了一声:“就是那头猪,这是被吃剩的。”话音未落,有人失声道:“那玩意儿,难道就在这附近?”
大黑狗突然纵身跳起,抖动着耳朵,发出阵阵低沉的吠叫。狗眼里冒出来兽性的凶狠,四条腿直直地挺立着,急促的摇摇尾巴,眦出如同刀锋一样锐利的牙齿。那牙齿,白生生的,在黑暗中看得格外的瘆人。二叔吸了口冷气,变了脸色:“那玩意儿就在这,咱们现在,怕是走不得了。”
大黑狗焦急地狂吠,蹬直了粗壮的后腿,随时准备扑过去。二叔将心一横,打了一声口哨。大黑狗一窜老远,直没入了黑暗里。二叔回过头看定几个同伴,脸上的表情有几分狰狞:“要走,你们只管走。我今天,要拼个鱼死网破”。
二叔一个人往前走去。他不用回头也知道,背后没有人跟上。他苦笑了一下,心头并不恨怨,反倒轻松了。生死有命,在此一搏。忽地,前面传来大黑狗,疯狂的吼叫声。大黑狗凶悍的战斗力,二叔是深知的。前年春天,村里闹开了狼,把村里的羊,先后拖走了四、五只。大黑狗被激怒了,不声不响地一路追踪,和狼群碰了个正着。最终大黑狗以一抵七,狗肚子被咬开,肠子都拖出来了,还是硬生生地咬死了七头饿狼。但现在面对的,是那个未知生物,大黑狗又有多少胜算呢?
据说人如果豁出去了一切,就不会畏惧死亡了。二叔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五响翻子”,直接冲了上去。



你们听说过哪些关于黄河的奇闻异事,历史故事?葭明通来说一段江苏徐州丰县废黄河变果园的历史故事吧!这个戈壁滩是怎么来的呢?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大沙河。起码应该有很多会读书懂科学的人来做这些工作才好!普通的农民群众是做不来这种工作的。然后就到了1957年!一致认为在“大沙河”应该直接种果树,尤其苹果树,不用搞什么防护林然后再造良田种庄稼的,不划算。遗惠今日!起码!在那个特殊年代,丰县征服了废黄河“小戈壁滩”,可以类比大寨梯田!
那是一个清晨,二叔去黄河边,取昨天晚上下好的网。让他意外的是,网里一条鱼也没有。却有一个透明的,乒乓球大小的物体。二叔有些好奇,用手指戳戳,感觉粘乎乎的。放在鼻子下面闻闻,有一股腥臭味,差点吐出来。
二叔很恼火,想把这个球状生物给扔了。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因为这个球状生物是活的,会扭来扭去。身体一会儿圆,一会儿扁,一会儿条。二叔看着有趣,就留了下来。
家中有个空置的水缸,二叔往里面倒了多半缸水,就把球状生物养在了里面。也许是怕太突兀了,还扔了五、六尾鲤鱼在里面。
二叔要忙去农活,一直到天擦黑,才回到了家里。想着早上捞的球状生物,便来到了水缸前。这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当真是吓了一跳。缸里的水,一片殷红。那生物倒还在缸里,只不过,已经变得有碗口那么大。缸里的五、六尾鲤鱼却只剩下了骨架,沉在了缸底。
二叔有些吃惊。这玩意儿,还能吃活鱼?他想了想,去厨下又捞了尾鲤鱼,投入了缸里。鲤鱼入缸,自由自在的游动着。没过多久,那个碗口大的生物,慢慢凑了过来,一下子便贴在了鲤鱼的身上。那鲤鱼拼命摆动,哪里挣脱的开?也就是眨眼睛的工夫,就被吞噬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缸里的水更是一片血红。
二叔倒抽了口冷气,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时,院里的长辈叫他去吃晚饭,他就暂时把这事儿给搁下了。等二叔再次想到这球状生物,已是第二天的晌午了。不知怎地,他心里有些发毛,人来到缸前,不禁又大吃一惊!
缸里只残留了一个篮球大小的透明膜儿,从中间撕裂了一个大洞,倒像是蜕下的皮。这玩意儿难道是跑了?二叔挠了挠头,在院里搜寻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也只好作罢了。
过了三、五天,二叔就把这事儿抛在了脑后。直到他有天傍晚收工回来,见邻居老王家门口,围了一大圈人。原来是老王媳妇儿站在门外“骂大街”,他才觉得是出了祸事!
老王家里,养了多年的一条黄狗。不吱声不吱气的,被吃得只剩下了骨架。老王媳妇儿那是一个泼辣女人,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这才站在自家门前破口大骂。二叔挤进了人群,看见了地上的黄狗骨架,打了个冷战。心头突突的乱跳,张嘴想说些什么,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二叔低着头,进了家门,他的心里很乱。第一,他不能确定,吃掉黄狗的,就是那个玩意儿。第二,就算说出来了,村里会有人信吗?第三,那玩意儿是他带回村里的,吃了一条黄狗事小,那老王媳妇儿却是出了名的泼辣货,二叔怎敢平白招惹?
一晃又过了几天,村子里风平浪静,什么事儿都没出。二叔松了一口气,暗暗庆幸自己沉得住气,没有吐露出别的。
事情就出在这天的上半夜。周家的小媳妇儿,爬起来给“大牲口棚”的牛、马添喂草料。她喂了一圈,独独不见家里那头健硕的水牛“老黑”。心头好生疑惑,这水牛能去哪里?又听得棚里隐约有些声响,便举着“煤油灯”细细看去。只见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水牛倒伏在角落,早没了气。大半边身子只剩下了森森白骨,一大团黑乎乎的的东西,将“老黑”紧紧裹住,还在不住的吞噬。周家小媳妇儿的那声尖叫:带着惶恐,带着愤怒,带着绝望。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几十年都过去了,原来谁也不曾忘却。
最先赶来的是周家的几个男人,他们看到了瘫倒在地上,崩溃的小媳妇儿。也看到了“牲口棚”里的可怕场景:那头水牛,只剩下小半段还有肉,大部分都成了骨架。但是吞噬水牛的东西,却没有了踪影。周家的人,脸都绿了,身子抖的厉害,就这么僵立着不动。村里人先后赶了过来,因为担心碰上了贼或者是野兽,不少男人手上还操着锄头、铁铲、木棒。
二叔也在人群当中,他的脸色苍白,如果不是手里握有一根木棒,都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等弄明白出了什么事,村民们面面相觑,一时没了主张,谁也不敢乱说话。
二叔大着胆子走进了“牲口棚”,举着“煤油灯”,里外又照了好一通。老周头看向他,紧张的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虎子,怎,怎么了?”二叔用木棒在地面戳了几下:“那东西,就藏在地里面”。
十几把锄头,铁铲在棚里挖了起来。挖了约摸半支烟的光景,村民们不再动手了,几十双眼睛,直勾勾 盯着翻挖出的泥土。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泥土上,沾染着大片大片鲜红的液体。村里的屠户用颤抖着的手沾了一点,只闻了闻,就变了脸色:“是牛血!”
二叔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睁开。他咬紧牙关,做了一个手势。村民们略略犹豫,便又挖了起来,约摸挖了十来分钟,村民们再次住了手。眼前的深坑里,有一大团鱼网状、深黑色的薄膜。如果完全铺展开来,那个面积怕是能覆盖住一头大象。二叔的头都大了,前后不过十来天,那玩意儿竟然生长得如此之大!
夜幕下,在村里的一处空旷所在,村民们牢牢地绑好了一口肥猪,估摸着也有二百多斤。屠户看准时机,在猪的喉咙上一刀刺入,伤口并不太深,那猪不断惨叫,鲜血汩汩地淌着。做好这一切,村民们各自寻好隐匿之处,埋伏起来静静的候着。
每个村民心中都忐忑不安,也不知等了多久,眼见得周围黑沉沉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鸟鸣。西北角的一株老树上,藏定一人,却是县里有名的老猎手。他伏在粗大的树干上,汗水自额头慢慢的渗出,他却一动也不动,只是用力紧握着那把猎枪。
二叔和老周家的,秉住了呼吸,各自蹲守在一口大水缸里。那大缸摆放在肥猪的两侧,双方相距不过两、三米远,每人手里都是一枝“五响翻子”。肥猪咽喉处的伤口越痛,便越挣扎。而肥猪越挣扎,血淌的便更多。不得不说,人是万物之灵。二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待那话儿现身,便打得它满身都是血窟窿眼。
蓦地,二叔只觉得脚下的大地,剧烈的抖动了起来。他小心翼翼的揭开缸盖,发现不远处鼓起了一个极大的土包,正一点一点的向肥猪的方向慢慢推进。他心里一紧,暗暗思量:终于等到你了!
土包的顶端,却在不停的蠕动着,分明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二叔长长的吐了口气,慢慢将手里的“五响翻子”对准了前方,手指因为紧张,微微有些发颤。他死命咬住下唇,都咬出血来了,这才稳住心神。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响,土包猛地翻了开来。二叔只瞧了一眼,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从缸里蹦出来。那土里冒出来的,竟然是成千上万只,又肥又大的灰毛老鼠!这老鼠群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便铺满了整个儿大地,疯狂的到处乱跑、乱钻。埋伏在四周的村民,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发一声喊,硬着头皮举起手中的锄头、铁铲奋力拍打。最奇的是,那些老鼠见了人,不但不怕,反而争先恐后的窜上身来,张口便咬。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眼见得数十个青壮年,人人身上都爬挂了无数只老鼠。村民们立刻乱了阵脚,有人实在撑不住了,撒开双腿,掉头往家中就跑。
树上的老猎人,对着躁动着的“鼠海”连连开了五、六枪,轰翻了一大片!但枪声、火药味儿,同类血肉模糊的尸体,受伤后翻滚挣扎的惨叫,一点儿也没有震慑到鼠群。老鼠们就像是疯了,完全是不管不顾的架式。二叔心里知道:完了!这混乱的局面,对村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他并不知道,这才刚刚拉开了序幕,真正的灭顶之灾还在后头呢。
二叔才窜出水缸,就遭到了几十只灰毛老鼠的疯狂撕咬,不到一分钟,身上就多处挂彩。他揩去脸上的血渍,飞快的打了声呼哨,一条黑狗便从不远处的灌木丛里窜出来。那黑狗体型巨大,好似牛犊大小,一看就知道非同寻常。二叔左手拍打着身上的老鼠,右手往鼠群一指,怒吼道:“老怪!给我狠狠的咬!”
黑狗的喉咙里发出炸雷似的声音,好不吓人!它准确的领会了主人的指令,从二叔身边一掠而过,箭一般迎着鼠群扑了上去。黑狗张开巨口,利如锋刃的狗牙横切竖割,草丛里,泥土里,黑狗的皮毛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攻击,鼠群起先是溃败的,但很快就开始了全面反击。黑狗即便再凶悍,面对成千上万的灰毛老鼠,也是绝无胜算!很快,狗血从浑身的十几个裂口中冒了出来,像是一条条小溪在无声的流淌。
但黑狗的战斗力是可怕的,竟然完全不在乎身上的伤势,仍在鼠群里左突右闯,前冲后撞,疯狂扑咬。这给了二叔一个机会。他跌跌撞撞,一头抢进了附近的一间“仓房”。那里摆放着木头、砖瓦、铁铲、锄头、马灯、煤油箱等杂物。他三两下扎好了一只“火把”,淋上了煤油,随手点燃,便冲了出来。
二叔咬牙切齿,手持“火把”,一步一步迎着鼠群走了过去。这一招极为有效,鼠群立时大乱。那老鼠见了火,如何不怕?纷纷退后,却不逃散,只围着“火把”团团打着转。二叔心里有数,胆子也更壮了,抢行几步,逼得鼠群又往后退了一段!口中大声喝道:“老周家的,叫上几个人,快去把村里的猫儿都赶过来!”
老周家的应了一声,撒腿就跑。在这乡下,家家几乎都养着猫儿避鼠的。天到这般时候,那些猫儿大多聚在一起,在茅屋外四下里游荡。二叔手中的“火把”此时虽旺,但鼠群似乎也明白,这火终会燃尽,并不远避。二叔心头焦躁,只盼着猫儿早些出来解困。忽见老周家的,抱着一只肥大的狸花猫,身后跟着五、六十个后生,每人怀里都抱着只猫儿,匆匆的赶了过来。
二叔心头,大喜过望。这猫和老鼠,是与生俱来的天敌。但凡是碰上了,必是要斗个不死不休。乡下的狸花猫,捕鼠更是能手。果然,那狸花猫看到老鼠,眼睛瞪得又大又圆。身上的毛倒竖起来,不待主人吩咐,喵的一声,便纵身一跃,扑了上去。这狸花猫实在是厉害,一口气便咬翻了数十只老鼠!那些个猫儿,见了老鼠,也都来了精神,一只接一只相继扑了上去,到处追咬。正在恶斗中的黑狗红了眼,它对身上的伤口已经麻木了。负了伤的黑狗没眨一下眼睛,就发动了新的进攻,必要置鼠群于死地。看准时机,黑狗发出一声声炸雷般的猛吼,化作黑色的旋风,朝前猛扑,又是一通死命撕咬。那鼠群虽说成千上万,但见了天敌,先自慌了。二叔和后生们,又先后点起了数十枝“火把”。鼠群再也扛不住了,四散奔逃,转眼间便逃得干干净净。
村民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过神来,看着满地血肉模糊的灰毛老鼠尸体,当真令人阵阵作呕,有些人更是张嘴吐了起来。二叔转脸,向那口肥猪的所在看去,不觉一怔,那头肥猪竟然不见了!二叔心里一慌,急忙奔到近前。方才只顾着和鼠群大战,地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大洞,黑洞洞的也不知深浅,那猪定是被拖入了洞穴深处。
二叔正犯着寻思,忽听得有人高喊道:“七爷,七爷怎么不见了?”那七爷便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一直藏身于西北角的老树上。好端端的,怎会不见了踪影?二叔找了一支手电,向下细细照去。赫然发现一只“长烟管”,正是七爷的心爱之物。想来,七爷定是看到肥猪被拖入了洞穴,他艺高人胆大,竟然也钻了进去。这时,有一些村民,也看出了情势不对,围了过来。
二叔把自己的推断,对众人简单的说了一下。便要带着黑狗下到洞穴,去接应七爷。众人哪肯让二叔一个人去犯险?当下选出来五、六个后生,人手一枝“五响翻子”,要陪着二叔一起探洞穴。
二叔打了个手势,黑狗便钻进了洞穴。二叔和那些后生,各自打着手电,紧紧地跟在黑狗的后面。那洞穴深处,却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虽然人人都拿着手电,也只不过能照亮前方两米的距离,再远的地方,那便是无尽的黑暗。
人在黑暗中行走,因为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心里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为防止发生意外,二叔特地又交代了一番。几个人在洞里走了几分钟后,大家的“方向感”就全没了。二叔倒不是太在意,只要有大黑狗在,这些都不算事儿。
走在队伍最后的,是一个叫大春的。他性子最是鲁莽,二叔怕他添乱,所以有意把他压在了队尾。说起来,大春是喝凉水塞牙缝,倒霉透了。在上个转弯处,他不小心崴脚了。按理来说,他应该立刻呼叫前面的队伍,但他为人过于好胜要强,暗暗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拖着右腿努力跟上。
又走了一段,大春的右腿脚踝处疼的越发厉害了。他用手电一照,自己也吓了一跳,那里肿的像是个馒头。他知道没法再跟下去,便对着前面大声喊着我二叔的名字:“虎子,虎子”。
二叔听见了,立刻摆手示意队伍停止前进,原地不动。大黑狗挺直了四腿,尾巴轻轻的晃了一下,在黑暗中的那双狗眼,闪闪发光。二叔拍了拍巨大的狗头,一个人向后找了过来。等两个人碰了面,二叔弄清了原委,又看了看大春的脚踝,耽搁不得。二叔当即决定,叫来一个后生,扶着大春原路返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后生搀扶着大春,打着手电慢慢的顺着来路往回走。才走了两个转弯口,大春就发现了问题,这路不对。周围实在是太黑了,两支手电筒照向远处,还是瞧得不太明白。大春黑着脸告诉后生:“我们方向走错了,这条路,我们压根没走过。”
后生是一脸懵逼。大春心里也觉得纳闷。这人下了洞穴,才走了多远?况且一路上,也没有看到有岔道啊。两人正犯着寻思,忽听得前方黑暗里,隐约传来几声狗吠。虽然听得不是很清,但大春和后生还是听出来了,是那只大黑狗发出的。
两人不禁呆了一呆。这是闹哪一出啊?怎么又绕到虎子那些人的前面来了?大春和后生想了想,还是打着手电,向着声音的方向摸了过去。
又走了好一段路,那狗吠声仍然是忽远忽近,飘忽不定,似是在引领着大春和后生。大春心里有些起疑,便站定了,不肯再往前去。后生的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安,在旁边悄声的说道:“大春哥,走了老半天了,那狗倒底在哪呢?要不,咱们喊两声试试?”
过了一会,大春轻声说道:“把手电都灭了”。后生微微一怔,随即照做了。四周顿时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大春又拉了拉后生的手,两人慢慢伏下身子。后生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这心跳得好厉害,和打鼓一般。
前面的黑暗处,又隐约传来了一些动静,但这次不是狗吠。大春慢慢用胳膊撞了撞身旁的后生,那人会意,两枝“五响翻子”同时顺过了枪管。又过了分把钟,只听得前面动静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仔细分辩,似乎是什么东西喘息的声音,好生的怪异。大春猛地打亮了手电,向前方照了过去。这手电的光亮并不好,但因为离的太近,大春和后生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大春那晚死在了当场,后生却侥幸活了下来,只是变成了疯子。后生一直到死,大伙儿在他嘴里,唯一听得明白的一句话是:“真的有鬼。”
走在最前面的大黑狗,忽然停了下来。摇晃着硕大的狗头,竖起了耳朵。不安的撮了撮鼻子,嗅着周围的空气,发出一阵粗闷的鼻息。二叔心里一紧,摸了摸那狗头。黑狗伸出舌头舔了舔二叔的手,不声不响地晃动着尾巴。二叔做了一个手势,大黑狗眦出了白森森的牙刀,伏低身子,慢慢地向前摸去。
转过弯来,大黑狗就在不远处,静静的卧着,无声的耸动着脸毛。二叔和三个伙伴,也随后赶了过来。几支手电照在了地上,大伙儿直瞧得脸色苍白,谁也作声不得。
地上扔着一把猎枪,那是县里有名儿的老猎人——七爷的心爱之物,枪身上却沾满了鲜血。二叔慢慢弯下腰,伸手去拾,那血,还没有全干!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句俗语:“枪在人在”的隐意。七爷如果还活着,断不会丢下这把猎枪。
二叔转脸问那几个同伴:“现在是回去,还是继续搜寻七爷?”一个后生鼓足了勇气,对二叔说:“虎子哥,七爷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他老人家都折在了这里,咱们还是先撤回去吧。”二叔知道这几个人是怕了,二叔自己心里也是有些发毛。
大黑狗却站了起来,暴躁地朝前跑了两步,又转回身来。前肢搭在二叔的身上,舔着二叔的手,轻轻的吠叫着。二叔想了想,还是跟着大黑狗向前走去。几个同伴略略迟疑,也都跟了上来。
约摸走了能有十来分钟,大黑狗再一次掉转过身来,绕着二叔兜起了圈子。洞穴里不通风,二叔等人提鼻子一闻,都不禁皱了皱眉头。前面传来的,是一股异味,熏得人一阵阵的作呕。几个人互相看了看,二叔冲他们摆了摆手,他一个人秉住这口气,悄悄的摸了过去。
手电照去,那是血肉模糊的一堆,有骨有肉。几个后生大着胆子摸了上来,看了一会儿,有人忍不住问道:“虎子哥,这会不会是?” 二叔“哼”了一声:“就是那头猪,这是被吃剩的。”话音未落,有人失声道:“那玩意儿,难道就在这附近?”
大黑狗突然纵身跳起,抖动着耳朵,发出阵阵低沉的吠叫。狗眼里冒出来兽性的凶狠,四条腿直直地挺立着,急促的摇摇尾巴,眦出如同刀锋一样锐利的牙齿。那牙齿,白生生的,在黑暗中看得格外的瘆人。二叔吸了口冷气,变了脸色:“那玩意儿就在这,咱们现在,怕是走不得了。”
大黑狗焦急地狂吠,蹬直了粗壮的后腿,随时准备扑过去。二叔将心一横,打了一声口哨。大黑狗一窜老远,直没入了黑暗里。二叔回过头看定几个同伴,脸上的表情有几分狰狞:“要走,你们只管走。我今天,要拼个鱼死网破”。
二叔一个人往前走去。他不用回头也知道,背后没有人跟上。他苦笑了一下,心头并不恨怨,反倒轻松了。生死有命,在此一搏。忽地,前面传来大黑狗,疯狂的吼叫声。大黑狗凶悍的战斗力,二叔是深知的。前年春天,村里闹开了狼,把村里的羊,先后拖走了四、五只。大黑狗被激怒了,不声不响地一路追踪,和狼群碰了个正着。最终大黑狗以一抵七,狗肚子被咬开,肠子都拖出来了,还是硬生生地咬死了七头饿狼。但现在面对的,是那个未知生物,大黑狗又有多少胜算呢?
据说人如果豁出去了一切,就不会畏惧死亡了。二叔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五响翻子”,直接冲了上去。



你们听说过哪些关于黄河的奇闻异事,历史故事?葭明通来说一段江苏徐州丰县废黄河变果园的历史故事吧!这个戈壁滩是怎么来的呢?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大沙河。起码应该有很多会读书懂科学的人来做这些工作才好!普通的农民群众是做不来这种工作的。然后就到了1957年!一致认为在“大沙河”应该直接种果树,尤其苹果树,不用搞什么防护林然后再造良田种庄稼的,不划算。遗惠今日!起码!在那个特殊年代,丰县征服了废黄河“小戈壁滩”,可以类比大寨梯田!
那是一个清晨,二叔去黄河边,取昨天晚上下好的网。让他意外的是,网里一条鱼也没有。却有一个透明的,乒乓球大小的物体。二叔有些好奇,用手指戳戳,感觉粘乎乎的。放在鼻子下面闻闻,有一股腥臭味,差点吐出来。
二叔很恼火,想把这个球状生物给扔了。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因为这个球状生物是活的,会扭来扭去。身体一会儿圆,一会儿扁,一会儿条。二叔看着有趣,就留了下来。
家中有个空置的水缸,二叔往里面倒了多半缸水,就把球状生物养在了里面。也许是怕太突兀了,还扔了五、六尾鲤鱼在里面。
二叔要忙去农活,一直到天擦黑,才回到了家里。想着早上捞的球状生物,便来到了水缸前。这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当真是吓了一跳。缸里的水,一片殷红。那生物倒还在缸里,只不过,已经变得有碗口那么大。缸里的五、六尾鲤鱼却只剩下了骨架,沉在了缸底。
二叔有些吃惊。这玩意儿,还能吃活鱼?他想了想,去厨下又捞了尾鲤鱼,投入了缸里。鲤鱼入缸,自由自在的游动着。没过多久,那个碗口大的生物,慢慢凑了过来,一下子便贴在了鲤鱼的身上。那鲤鱼拼命摆动,哪里挣脱的开?也就是眨眼睛的工夫,就被吞噬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缸里的水更是一片血红。
二叔倒抽了口冷气,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时,院里的长辈叫他去吃晚饭,他就暂时把这事儿给搁下了。等二叔再次想到这球状生物,已是第二天的晌午了。不知怎地,他心里有些发毛,人来到缸前,不禁又大吃一惊!
缸里只残留了一个篮球大小的透明膜儿,从中间撕裂了一个大洞,倒像是蜕下的皮。这玩意儿难道是跑了?二叔挠了挠头,在院里搜寻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也只好作罢了。
过了三、五天,二叔就把这事儿抛在了脑后。直到他有天傍晚收工回来,见邻居老王家门口,围了一大圈人。原来是老王媳妇儿站在门外“骂大街”,他才觉得是出了祸事!
老王家里,养了多年的一条黄狗。不吱声不吱气的,被吃得只剩下了骨架。老王媳妇儿那是一个泼辣女人,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这才站在自家门前破口大骂。二叔挤进了人群,看见了地上的黄狗骨架,打了个冷战。心头突突的乱跳,张嘴想说些什么,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二叔低着头,进了家门,他的心里很乱。第一,他不能确定,吃掉黄狗的,就是那个玩意儿。第二,就算说出来了,村里会有人信吗?第三,那玩意儿是他带回村里的,吃了一条黄狗事小,那老王媳妇儿却是出了名的泼辣货,二叔怎敢平白招惹?
一晃又过了几天,村子里风平浪静,什么事儿都没出。二叔松了一口气,暗暗庆幸自己沉得住气,没有吐露出别的。
事情就出在这天的上半夜。周家的小媳妇儿,爬起来给“大牲口棚”的牛、马添喂草料。她喂了一圈,独独不见家里那头健硕的水牛“老黑”。心头好生疑惑,这水牛能去哪里?又听得棚里隐约有些声响,便举着“煤油灯”细细看去。只见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水牛倒伏在角落,早没了气。大半边身子只剩下了森森白骨,一大团黑乎乎的的东西,将“老黑”紧紧裹住,还在不住的吞噬。周家小媳妇儿的那声尖叫:带着惶恐,带着愤怒,带着绝望。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几十年都过去了,原来谁也不曾忘却。
最先赶来的是周家的几个男人,他们看到了瘫倒在地上,崩溃的小媳妇儿。也看到了“牲口棚”里的可怕场景:那头水牛,只剩下小半段还有肉,大部分都成了骨架。但是吞噬水牛的东西,却没有了踪影。周家的人,脸都绿了,身子抖的厉害,就这么僵立着不动。村里人先后赶了过来,因为担心碰上了贼或者是野兽,不少男人手上还操着锄头、铁铲、木棒。
二叔也在人群当中,他的脸色苍白,如果不是手里握有一根木棒,都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等弄明白出了什么事,村民们面面相觑,一时没了主张,谁也不敢乱说话。
二叔大着胆子走进了“牲口棚”,举着“煤油灯”,里外又照了好一通。老周头看向他,紧张的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虎子,怎,怎么了?”二叔用木棒在地面戳了几下:“那东西,就藏在地里面”。
十几把锄头,铁铲在棚里挖了起来。挖了约摸半支烟的光景,村民们不再动手了,几十双眼睛,直勾勾 盯着翻挖出的泥土。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泥土上,沾染着大片大片鲜红的液体。村里的屠户用颤抖着的手沾了一点,只闻了闻,就变了脸色:“是牛血!”
二叔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睁开。他咬紧牙关,做了一个手势。村民们略略犹豫,便又挖了起来,约摸挖了十来分钟,村民们再次住了手。眼前的深坑里,有一大团鱼网状、深黑色的薄膜。如果完全铺展开来,那个面积怕是能覆盖住一头大象。二叔的头都大了,前后不过十来天,那玩意儿竟然生长得如此之大!
夜幕下,在村里的一处空旷所在,村民们牢牢地绑好了一口肥猪,估摸着也有二百多斤。屠户看准时机,在猪的喉咙上一刀刺入,伤口并不太深,那猪不断惨叫,鲜血汩汩地淌着。做好这一切,村民们各自寻好隐匿之处,埋伏起来静静的候着。
每个村民心中都忐忑不安,也不知等了多久,眼见得周围黑沉沉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鸟鸣。西北角的一株老树上,藏定一人,却是县里有名的老猎手。他伏在粗大的树干上,汗水自额头慢慢的渗出,他却一动也不动,只是用力紧握着那把猎枪。
二叔和老周家的,秉住了呼吸,各自蹲守在一口大水缸里。那大缸摆放在肥猪的两侧,双方相距不过两、三米远,每人手里都是一枝“五响翻子”。肥猪咽喉处的伤口越痛,便越挣扎。而肥猪越挣扎,血淌的便更多。不得不说,人是万物之灵。二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待那话儿现身,便打得它满身都是血窟窿眼。
蓦地,二叔只觉得脚下的大地,剧烈的抖动了起来。他小心翼翼的揭开缸盖,发现不远处鼓起了一个极大的土包,正一点一点的向肥猪的方向慢慢推进。他心里一紧,暗暗思量:终于等到你了!
土包的顶端,却在不停的蠕动着,分明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二叔长长的吐了口气,慢慢将手里的“五响翻子”对准了前方,手指因为紧张,微微有些发颤。他死命咬住下唇,都咬出血来了,这才稳住心神。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响,土包猛地翻了开来。二叔只瞧了一眼,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从缸里蹦出来。那土里冒出来的,竟然是成千上万只,又肥又大的灰毛老鼠!这老鼠群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便铺满了整个儿大地,疯狂的到处乱跑、乱钻。埋伏在四周的村民,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发一声喊,硬着头皮举起手中的锄头、铁铲奋力拍打。最奇的是,那些老鼠见了人,不但不怕,反而争先恐后的窜上身来,张口便咬。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眼见得数十个青壮年,人人身上都爬挂了无数只老鼠。村民们立刻乱了阵脚,有人实在撑不住了,撒开双腿,掉头往家中就跑。
树上的老猎人,对着躁动着的“鼠海”连连开了五、六枪,轰翻了一大片!但枪声、火药味儿,同类血肉模糊的尸体,受伤后翻滚挣扎的惨叫,一点儿也没有震慑到鼠群。老鼠们就像是疯了,完全是不管不顾的架式。二叔心里知道:完了!这混乱的局面,对村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他并不知道,这才刚刚拉开了序幕,真正的灭顶之灾还在后头呢。
二叔才窜出水缸,就遭到了几十只灰毛老鼠的疯狂撕咬,不到一分钟,身上就多处挂彩。他揩去脸上的血渍,飞快的打了声呼哨,一条黑狗便从不远处的灌木丛里窜出来。那黑狗体型巨大,好似牛犊大小,一看就知道非同寻常。二叔左手拍打着身上的老鼠,右手往鼠群一指,怒吼道:“老怪!给我狠狠的咬!”
黑狗的喉咙里发出炸雷似的声音,好不吓人!它准确的领会了主人的指令,从二叔身边一掠而过,箭一般迎着鼠群扑了上去。黑狗张开巨口,利如锋刃的狗牙横切竖割,草丛里,泥土里,黑狗的皮毛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攻击,鼠群起先是溃败的,但很快就开始了全面反击。黑狗即便再凶悍,面对成千上万的灰毛老鼠,也是绝无胜算!很快,狗血从浑身的十几个裂口中冒了出来,像是一条条小溪在无声的流淌。
但黑狗的战斗力是可怕的,竟然完全不在乎身上的伤势,仍在鼠群里左突右闯,前冲后撞,疯狂扑咬。这给了二叔一个机会。他跌跌撞撞,一头抢进了附近的一间“仓房”。那里摆放着木头、砖瓦、铁铲、锄头、马灯、煤油箱等杂物。他三两下扎好了一只“火把”,淋上了煤油,随手点燃,便冲了出来。
二叔咬牙切齿,手持“火把”,一步一步迎着鼠群走了过去。这一招极为有效,鼠群立时大乱。那老鼠见了火,如何不怕?纷纷退后,却不逃散,只围着“火把”团团打着转。二叔心里有数,胆子也更壮了,抢行几步,逼得鼠群又往后退了一段!口中大声喝道:“老周家的,叫上几个人,快去把村里的猫儿都赶过来!”
老周家的应了一声,撒腿就跑。在这乡下,家家几乎都养着猫儿避鼠的。天到这般时候,那些猫儿大多聚在一起,在茅屋外四下里游荡。二叔手中的“火把”此时虽旺,但鼠群似乎也明白,这火终会燃尽,并不远避。二叔心头焦躁,只盼着猫儿早些出来解困。忽见老周家的,抱着一只肥大的狸花猫,身后跟着五、六十个后生,每人怀里都抱着只猫儿,匆匆的赶了过来。
二叔心头,大喜过望。这猫和老鼠,是与生俱来的天敌。但凡是碰上了,必是要斗个不死不休。乡下的狸花猫,捕鼠更是能手。果然,那狸花猫看到老鼠,眼睛瞪得又大又圆。身上的毛倒竖起来,不待主人吩咐,喵的一声,便纵身一跃,扑了上去。这狸花猫实在是厉害,一口气便咬翻了数十只老鼠!那些个猫儿,见了老鼠,也都来了精神,一只接一只相继扑了上去,到处追咬。正在恶斗中的黑狗红了眼,它对身上的伤口已经麻木了。负了伤的黑狗没眨一下眼睛,就发动了新的进攻,必要置鼠群于死地。看准时机,黑狗发出一声声炸雷般的猛吼,化作黑色的旋风,朝前猛扑,又是一通死命撕咬。那鼠群虽说成千上万,但见了天敌,先自慌了。二叔和后生们,又先后点起了数十枝“火把”。鼠群再也扛不住了,四散奔逃,转眼间便逃得干干净净。
村民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过神来,看着满地血肉模糊的灰毛老鼠尸体,当真令人阵阵作呕,有些人更是张嘴吐了起来。二叔转脸,向那口肥猪的所在看去,不觉一怔,那头肥猪竟然不见了!二叔心里一慌,急忙奔到近前。方才只顾着和鼠群大战,地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大洞,黑洞洞的也不知深浅,那猪定是被拖入了洞穴深处。
二叔正犯着寻思,忽听得有人高喊道:“七爷,七爷怎么不见了?”那七爷便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一直藏身于西北角的老树上。好端端的,怎会不见了踪影?二叔找了一支手电,向下细细照去。赫然发现一只“长烟管”,正是七爷的心爱之物。想来,七爷定是看到肥猪被拖入了洞穴,他艺高人胆大,竟然也钻了进去。这时,有一些村民,也看出了情势不对,围了过来。
二叔把自己的推断,对众人简单的说了一下。便要带着黑狗下到洞穴,去接应七爷。众人哪肯让二叔一个人去犯险?当下选出来五、六个后生,人手一枝“五响翻子”,要陪着二叔一起探洞穴。
二叔打了个手势,黑狗便钻进了洞穴。二叔和那些后生,各自打着手电,紧紧地跟在黑狗的后面。那洞穴深处,却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虽然人人都拿着手电,也只不过能照亮前方两米的距离,再远的地方,那便是无尽的黑暗。
人在黑暗中行走,因为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心里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为防止发生意外,二叔特地又交代了一番。几个人在洞里走了几分钟后,大家的“方向感”就全没了。二叔倒不是太在意,只要有大黑狗在,这些都不算事儿。
走在队伍最后的,是一个叫大春的。他性子最是鲁莽,二叔怕他添乱,所以有意把他压在了队尾。说起来,大春是喝凉水塞牙缝,倒霉透了。在上个转弯处,他不小心崴脚了。按理来说,他应该立刻呼叫前面的队伍,但他为人过于好胜要强,暗暗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拖着右腿努力跟上。
又走了一段,大春的右腿脚踝处疼的越发厉害了。他用手电一照,自己也吓了一跳,那里肿的像是个馒头。他知道没法再跟下去,便对着前面大声喊着我二叔的名字:“虎子,虎子”。
二叔听见了,立刻摆手示意队伍停止前进,原地不动。大黑狗挺直了四腿,尾巴轻轻的晃了一下,在黑暗中的那双狗眼,闪闪发光。二叔拍了拍巨大的狗头,一个人向后找了过来。等两个人碰了面,二叔弄清了原委,又看了看大春的脚踝,耽搁不得。二叔当即决定,叫来一个后生,扶着大春原路返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后生搀扶着大春,打着手电慢慢的顺着来路往回走。才走了两个转弯口,大春就发现了问题,这路不对。周围实在是太黑了,两支手电筒照向远处,还是瞧得不太明白。大春黑着脸告诉后生:“我们方向走错了,这条路,我们压根没走过。”
后生是一脸懵逼。大春心里也觉得纳闷。这人下了洞穴,才走了多远?况且一路上,也没有看到有岔道啊。两人正犯着寻思,忽听得前方黑暗里,隐约传来几声狗吠。虽然听得不是很清,但大春和后生还是听出来了,是那只大黑狗发出的。
两人不禁呆了一呆。这是闹哪一出啊?怎么又绕到虎子那些人的前面来了?大春和后生想了想,还是打着手电,向着声音的方向摸了过去。
又走了好一段路,那狗吠声仍然是忽远忽近,飘忽不定,似是在引领着大春和后生。大春心里有些起疑,便站定了,不肯再往前去。后生的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安,在旁边悄声的说道:“大春哥,走了老半天了,那狗倒底在哪呢?要不,咱们喊两声试试?”
过了一会,大春轻声说道:“把手电都灭了”。后生微微一怔,随即照做了。四周顿时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大春又拉了拉后生的手,两人慢慢伏下身子。后生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这心跳得好厉害,和打鼓一般。
前面的黑暗处,又隐约传来了一些动静,但这次不是狗吠。大春慢慢用胳膊撞了撞身旁的后生,那人会意,两枝“五响翻子”同时顺过了枪管。又过了分把钟,只听得前面动静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仔细分辩,似乎是什么东西喘息的声音,好生的怪异。大春猛地打亮了手电,向前方照了过去。这手电的光亮并不好,但因为离的太近,大春和后生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大春那晚死在了当场,后生却侥幸活了下来,只是变成了疯子。后生一直到死,大伙儿在他嘴里,唯一听得明白的一句话是:“真的有鬼。”
走在最前面的大黑狗,忽然停了下来。摇晃着硕大的狗头,竖起了耳朵。不安的撮了撮鼻子,嗅着周围的空气,发出一阵粗闷的鼻息。二叔心里一紧,摸了摸那狗头。黑狗伸出舌头舔了舔二叔的手,不声不响地晃动着尾巴。二叔做了一个手势,大黑狗眦出了白森森的牙刀,伏低身子,慢慢地向前摸去。
转过弯来,大黑狗就在不远处,静静的卧着,无声的耸动着脸毛。二叔和三个伙伴,也随后赶了过来。几支手电照在了地上,大伙儿直瞧得脸色苍白,谁也作声不得。
地上扔着一把猎枪,那是县里有名儿的老猎人——七爷的心爱之物,枪身上却沾满了鲜血。二叔慢慢弯下腰,伸手去拾,那血,还没有全干!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句俗语:“枪在人在”的隐意。七爷如果还活着,断不会丢下这把猎枪。
二叔转脸问那几个同伴:“现在是回去,还是继续搜寻七爷?”一个后生鼓足了勇气,对二叔说:“虎子哥,七爷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他老人家都折在了这里,咱们还是先撤回去吧。”二叔知道这几个人是怕了,二叔自己心里也是有些发毛。
大黑狗却站了起来,暴躁地朝前跑了两步,又转回身来。前肢搭在二叔的身上,舔着二叔的手,轻轻的吠叫着。二叔想了想,还是跟着大黑狗向前走去。几个同伴略略迟疑,也都跟了上来。
约摸走了能有十来分钟,大黑狗再一次掉转过身来,绕着二叔兜起了圈子。洞穴里不通风,二叔等人提鼻子一闻,都不禁皱了皱眉头。前面传来的,是一股异味,熏得人一阵阵的作呕。几个人互相看了看,二叔冲他们摆了摆手,他一个人秉住这口气,悄悄的摸了过去。
手电照去,那是血肉模糊的一堆,有骨有肉。几个后生大着胆子摸了上来,看了一会儿,有人忍不住问道:“虎子哥,这会不会是?” 二叔“哼”了一声:“就是那头猪,这是被吃剩的。”话音未落,有人失声道:“那玩意儿,难道就在这附近?”
大黑狗突然纵身跳起,抖动着耳朵,发出阵阵低沉的吠叫。狗眼里冒出来兽性的凶狠,四条腿直直地挺立着,急促的摇摇尾巴,眦出如同刀锋一样锐利的牙齿。那牙齿,白生生的,在黑暗中看得格外的瘆人。二叔吸了口冷气,变了脸色:“那玩意儿就在这,咱们现在,怕是走不得了。”
大黑狗焦急地狂吠,蹬直了粗壮的后腿,随时准备扑过去。二叔将心一横,打了一声口哨。大黑狗一窜老远,直没入了黑暗里。二叔回过头看定几个同伴,脸上的表情有几分狰狞:“要走,你们只管走。我今天,要拼个鱼死网破”。
二叔一个人往前走去。他不用回头也知道,背后没有人跟上。他苦笑了一下,心头并不恨怨,反倒轻松了。生死有命,在此一搏。忽地,前面传来大黑狗,疯狂的吼叫声。大黑狗凶悍的战斗力,二叔是深知的。前年春天,村里闹开了狼,把村里的羊,先后拖走了四、五只。大黑狗被激怒了,不声不响地一路追踪,和狼群碰了个正着。最终大黑狗以一抵七,狗肚子被咬开,肠子都拖出来了,还是硬生生地咬死了七头饿狼。但现在面对的,是那个未知生物,大黑狗又有多少胜算呢?
据说人如果豁出去了一切,就不会畏惧死亡了。二叔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五响翻子”,直接冲了上去。



你们听说过哪些关于黄河的奇闻异事,历史故事?葭明通来说一段江苏徐州丰县废黄河变果园的历史故事吧!这个戈壁滩是怎么来的呢?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大沙河。起码应该有很多会读书懂科学的人来做这些工作才好!普通的农民群众是做不来这种工作的。然后就到了1957年!一致认为在“大沙河”应该直接种果树,尤其苹果树,不用搞什么防护林然后再造良田种庄稼的,不划算。遗惠今日!起码!在那个特殊年代,丰县征服了废黄河“小戈壁滩”,可以类比大寨梯田!
那是一个清晨,二叔去黄河边,取昨天晚上下好的网。让他意外的是,网里一条鱼也没有。却有一个透明的,乒乓球大小的物体。二叔有些好奇,用手指戳戳,感觉粘乎乎的。放在鼻子下面闻闻,有一股腥臭味,差点吐出来。
二叔很恼火,想把这个球状生物给扔了。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因为这个球状生物是活的,会扭来扭去。身体一会儿圆,一会儿扁,一会儿条。二叔看着有趣,就留了下来。
家中有个空置的水缸,二叔往里面倒了多半缸水,就把球状生物养在了里面。也许是怕太突兀了,还扔了五、六尾鲤鱼在里面。
二叔要忙去农活,一直到天擦黑,才回到了家里。想着早上捞的球状生物,便来到了水缸前。这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当真是吓了一跳。缸里的水,一片殷红。那生物倒还在缸里,只不过,已经变得有碗口那么大。缸里的五、六尾鲤鱼却只剩下了骨架,沉在了缸底。
二叔有些吃惊。这玩意儿,还能吃活鱼?他想了想,去厨下又捞了尾鲤鱼,投入了缸里。鲤鱼入缸,自由自在的游动着。没过多久,那个碗口大的生物,慢慢凑了过来,一下子便贴在了鲤鱼的身上。那鲤鱼拼命摆动,哪里挣脱的开?也就是眨眼睛的工夫,就被吞噬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缸里的水更是一片血红。
二叔倒抽了口冷气,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时,院里的长辈叫他去吃晚饭,他就暂时把这事儿给搁下了。等二叔再次想到这球状生物,已是第二天的晌午了。不知怎地,他心里有些发毛,人来到缸前,不禁又大吃一惊!
缸里只残留了一个篮球大小的透明膜儿,从中间撕裂了一个大洞,倒像是蜕下的皮。这玩意儿难道是跑了?二叔挠了挠头,在院里搜寻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也只好作罢了。
过了三、五天,二叔就把这事儿抛在了脑后。直到他有天傍晚收工回来,见邻居老王家门口,围了一大圈人。原来是老王媳妇儿站在门外“骂大街”,他才觉得是出了祸事!
老王家里,养了多年的一条黄狗。不吱声不吱气的,被吃得只剩下了骨架。老王媳妇儿那是一个泼辣女人,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这才站在自家门前破口大骂。二叔挤进了人群,看见了地上的黄狗骨架,打了个冷战。心头突突的乱跳,张嘴想说些什么,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二叔低着头,进了家门,他的心里很乱。第一,他不能确定,吃掉黄狗的,就是那个玩意儿。第二,就算说出来了,村里会有人信吗?第三,那玩意儿是他带回村里的,吃了一条黄狗事小,那老王媳妇儿却是出了名的泼辣货,二叔怎敢平白招惹?
一晃又过了几天,村子里风平浪静,什么事儿都没出。二叔松了一口气,暗暗庆幸自己沉得住气,没有吐露出别的。
事情就出在这天的上半夜。周家的小媳妇儿,爬起来给“大牲口棚”的牛、马添喂草料。她喂了一圈,独独不见家里那头健硕的水牛“老黑”。心头好生疑惑,这水牛能去哪里?又听得棚里隐约有些声响,便举着“煤油灯”细细看去。只见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水牛倒伏在角落,早没了气。大半边身子只剩下了森森白骨,一大团黑乎乎的的东西,将“老黑”紧紧裹住,还在不住的吞噬。周家小媳妇儿的那声尖叫:带着惶恐,带着愤怒,带着绝望。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几十年都过去了,原来谁也不曾忘却。
最先赶来的是周家的几个男人,他们看到了瘫倒在地上,崩溃的小媳妇儿。也看到了“牲口棚”里的可怕场景:那头水牛,只剩下小半段还有肉,大部分都成了骨架。但是吞噬水牛的东西,却没有了踪影。周家的人,脸都绿了,身子抖的厉害,就这么僵立着不动。村里人先后赶了过来,因为担心碰上了贼或者是野兽,不少男人手上还操着锄头、铁铲、木棒。
二叔也在人群当中,他的脸色苍白,如果不是手里握有一根木棒,都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等弄明白出了什么事,村民们面面相觑,一时没了主张,谁也不敢乱说话。
二叔大着胆子走进了“牲口棚”,举着“煤油灯”,里外又照了好一通。老周头看向他,紧张的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虎子,怎,怎么了?”二叔用木棒在地面戳了几下:“那东西,就藏在地里面”。
十几把锄头,铁铲在棚里挖了起来。挖了约摸半支烟的光景,村民们不再动手了,几十双眼睛,直勾勾 盯着翻挖出的泥土。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泥土上,沾染着大片大片鲜红的液体。村里的屠户用颤抖着的手沾了一点,只闻了闻,就变了脸色:“是牛血!”
二叔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睁开。他咬紧牙关,做了一个手势。村民们略略犹豫,便又挖了起来,约摸挖了十来分钟,村民们再次住了手。眼前的深坑里,有一大团鱼网状、深黑色的薄膜。如果完全铺展开来,那个面积怕是能覆盖住一头大象。二叔的头都大了,前后不过十来天,那玩意儿竟然生长得如此之大!
夜幕下,在村里的一处空旷所在,村民们牢牢地绑好了一口肥猪,估摸着也有二百多斤。屠户看准时机,在猪的喉咙上一刀刺入,伤口并不太深,那猪不断惨叫,鲜血汩汩地淌着。做好这一切,村民们各自寻好隐匿之处,埋伏起来静静的候着。
每个村民心中都忐忑不安,也不知等了多久,眼见得周围黑沉沉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鸟鸣。西北角的一株老树上,藏定一人,却是县里有名的老猎手。他伏在粗大的树干上,汗水自额头慢慢的渗出,他却一动也不动,只是用力紧握着那把猎枪。
二叔和老周家的,秉住了呼吸,各自蹲守在一口大水缸里。那大缸摆放在肥猪的两侧,双方相距不过两、三米远,每人手里都是一枝“五响翻子”。肥猪咽喉处的伤口越痛,便越挣扎。而肥猪越挣扎,血淌的便更多。不得不说,人是万物之灵。二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待那话儿现身,便打得它满身都是血窟窿眼。
蓦地,二叔只觉得脚下的大地,剧烈的抖动了起来。他小心翼翼的揭开缸盖,发现不远处鼓起了一个极大的土包,正一点一点的向肥猪的方向慢慢推进。他心里一紧,暗暗思量:终于等到你了!
土包的顶端,却在不停的蠕动着,分明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二叔长长的吐了口气,慢慢将手里的“五响翻子”对准了前方,手指因为紧张,微微有些发颤。他死命咬住下唇,都咬出血来了,这才稳住心神。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响,土包猛地翻了开来。二叔只瞧了一眼,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从缸里蹦出来。那土里冒出来的,竟然是成千上万只,又肥又大的灰毛老鼠!这老鼠群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便铺满了整个儿大地,疯狂的到处乱跑、乱钻。埋伏在四周的村民,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发一声喊,硬着头皮举起手中的锄头、铁铲奋力拍打。最奇的是,那些老鼠见了人,不但不怕,反而争先恐后的窜上身来,张口便咬。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眼见得数十个青壮年,人人身上都爬挂了无数只老鼠。村民们立刻乱了阵脚,有人实在撑不住了,撒开双腿,掉头往家中就跑。
树上的老猎人,对着躁动着的“鼠海”连连开了五、六枪,轰翻了一大片!但枪声、火药味儿,同类血肉模糊的尸体,受伤后翻滚挣扎的惨叫,一点儿也没有震慑到鼠群。老鼠们就像是疯了,完全是不管不顾的架式。二叔心里知道:完了!这混乱的局面,对村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他并不知道,这才刚刚拉开了序幕,真正的灭顶之灾还在后头呢。
二叔才窜出水缸,就遭到了几十只灰毛老鼠的疯狂撕咬,不到一分钟,身上就多处挂彩。他揩去脸上的血渍,飞快的打了声呼哨,一条黑狗便从不远处的灌木丛里窜出来。那黑狗体型巨大,好似牛犊大小,一看就知道非同寻常。二叔左手拍打着身上的老鼠,右手往鼠群一指,怒吼道:“老怪!给我狠狠的咬!”
黑狗的喉咙里发出炸雷似的声音,好不吓人!它准确的领会了主人的指令,从二叔身边一掠而过,箭一般迎着鼠群扑了上去。黑狗张开巨口,利如锋刃的狗牙横切竖割,草丛里,泥土里,黑狗的皮毛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攻击,鼠群起先是溃败的,但很快就开始了全面反击。黑狗即便再凶悍,面对成千上万的灰毛老鼠,也是绝无胜算!很快,狗血从浑身的十几个裂口中冒了出来,像是一条条小溪在无声的流淌。
但黑狗的战斗力是可怕的,竟然完全不在乎身上的伤势,仍在鼠群里左突右闯,前冲后撞,疯狂扑咬。这给了二叔一个机会。他跌跌撞撞,一头抢进了附近的一间“仓房”。那里摆放着木头、砖瓦、铁铲、锄头、马灯、煤油箱等杂物。他三两下扎好了一只“火把”,淋上了煤油,随手点燃,便冲了出来。
二叔咬牙切齿,手持“火把”,一步一步迎着鼠群走了过去。这一招极为有效,鼠群立时大乱。那老鼠见了火,如何不怕?纷纷退后,却不逃散,只围着“火把”团团打着转。二叔心里有数,胆子也更壮了,抢行几步,逼得鼠群又往后退了一段!口中大声喝道:“老周家的,叫上几个人,快去把村里的猫儿都赶过来!”
老周家的应了一声,撒腿就跑。在这乡下,家家几乎都养着猫儿避鼠的。天到这般时候,那些猫儿大多聚在一起,在茅屋外四下里游荡。二叔手中的“火把”此时虽旺,但鼠群似乎也明白,这火终会燃尽,并不远避。二叔心头焦躁,只盼着猫儿早些出来解困。忽见老周家的,抱着一只肥大的狸花猫,身后跟着五、六十个后生,每人怀里都抱着只猫儿,匆匆的赶了过来。
二叔心头,大喜过望。这猫和老鼠,是与生俱来的天敌。但凡是碰上了,必是要斗个不死不休。乡下的狸花猫,捕鼠更是能手。果然,那狸花猫看到老鼠,眼睛瞪得又大又圆。身上的毛倒竖起来,不待主人吩咐,喵的一声,便纵身一跃,扑了上去。这狸花猫实在是厉害,一口气便咬翻了数十只老鼠!那些个猫儿,见了老鼠,也都来了精神,一只接一只相继扑了上去,到处追咬。正在恶斗中的黑狗红了眼,它对身上的伤口已经麻木了。负了伤的黑狗没眨一下眼睛,就发动了新的进攻,必要置鼠群于死地。看准时机,黑狗发出一声声炸雷般的猛吼,化作黑色的旋风,朝前猛扑,又是一通死命撕咬。那鼠群虽说成千上万,但见了天敌,先自慌了。二叔和后生们,又先后点起了数十枝“火把”。鼠群再也扛不住了,四散奔逃,转眼间便逃得干干净净。
村民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过神来,看着满地血肉模糊的灰毛老鼠尸体,当真令人阵阵作呕,有些人更是张嘴吐了起来。二叔转脸,向那口肥猪的所在看去,不觉一怔,那头肥猪竟然不见了!二叔心里一慌,急忙奔到近前。方才只顾着和鼠群大战,地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大洞,黑洞洞的也不知深浅,那猪定是被拖入了洞穴深处。
二叔正犯着寻思,忽听得有人高喊道:“七爷,七爷怎么不见了?”那七爷便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一直藏身于西北角的老树上。好端端的,怎会不见了踪影?二叔找了一支手电,向下细细照去。赫然发现一只“长烟管”,正是七爷的心爱之物。想来,七爷定是看到肥猪被拖入了洞穴,他艺高人胆大,竟然也钻了进去。这时,有一些村民,也看出了情势不对,围了过来。
二叔把自己的推断,对众人简单的说了一下。便要带着黑狗下到洞穴,去接应七爷。众人哪肯让二叔一个人去犯险?当下选出来五、六个后生,人手一枝“五响翻子”,要陪着二叔一起探洞穴。
二叔打了个手势,黑狗便钻进了洞穴。二叔和那些后生,各自打着手电,紧紧地跟在黑狗的后面。那洞穴深处,却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虽然人人都拿着手电,也只不过能照亮前方两米的距离,再远的地方,那便是无尽的黑暗。
人在黑暗中行走,因为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心里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为防止发生意外,二叔特地又交代了一番。几个人在洞里走了几分钟后,大家的“方向感”就全没了。二叔倒不是太在意,只要有大黑狗在,这些都不算事儿。
走在队伍最后的,是一个叫大春的。他性子最是鲁莽,二叔怕他添乱,所以有意把他压在了队尾。说起来,大春是喝凉水塞牙缝,倒霉透了。在上个转弯处,他不小心崴脚了。按理来说,他应该立刻呼叫前面的队伍,但他为人过于好胜要强,暗暗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拖着右腿努力跟上。
又走了一段,大春的右腿脚踝处疼的越发厉害了。他用手电一照,自己也吓了一跳,那里肿的像是个馒头。他知道没法再跟下去,便对着前面大声喊着我二叔的名字:“虎子,虎子”。
二叔听见了,立刻摆手示意队伍停止前进,原地不动。大黑狗挺直了四腿,尾巴轻轻的晃了一下,在黑暗中的那双狗眼,闪闪发光。二叔拍了拍巨大的狗头,一个人向后找了过来。等两个人碰了面,二叔弄清了原委,又看了看大春的脚踝,耽搁不得。二叔当即决定,叫来一个后生,扶着大春原路返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后生搀扶着大春,打着手电慢慢的顺着来路往回走。才走了两个转弯口,大春就发现了问题,这路不对。周围实在是太黑了,两支手电筒照向远处,还是瞧得不太明白。大春黑着脸告诉后生:“我们方向走错了,这条路,我们压根没走过。”
后生是一脸懵逼。大春心里也觉得纳闷。这人下了洞穴,才走了多远?况且一路上,也没有看到有岔道啊。两人正犯着寻思,忽听得前方黑暗里,隐约传来几声狗吠。虽然听得不是很清,但大春和后生还是听出来了,是那只大黑狗发出的。
两人不禁呆了一呆。这是闹哪一出啊?怎么又绕到虎子那些人的前面来了?大春和后生想了想,还是打着手电,向着声音的方向摸了过去。
又走了好一段路,那狗吠声仍然是忽远忽近,飘忽不定,似是在引领着大春和后生。大春心里有些起疑,便站定了,不肯再往前去。后生的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安,在旁边悄声的说道:“大春哥,走了老半天了,那狗倒底在哪呢?要不,咱们喊两声试试?”
过了一会,大春轻声说道:“把手电都灭了”。后生微微一怔,随即照做了。四周顿时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大春又拉了拉后生的手,两人慢慢伏下身子。后生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这心跳得好厉害,和打鼓一般。
前面的黑暗处,又隐约传来了一些动静,但这次不是狗吠。大春慢慢用胳膊撞了撞身旁的后生,那人会意,两枝“五响翻子”同时顺过了枪管。又过了分把钟,只听得前面动静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仔细分辩,似乎是什么东西喘息的声音,好生的怪异。大春猛地打亮了手电,向前方照了过去。这手电的光亮并不好,但因为离的太近,大春和后生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大春那晚死在了当场,后生却侥幸活了下来,只是变成了疯子。后生一直到死,大伙儿在他嘴里,唯一听得明白的一句话是:“真的有鬼。”
走在最前面的大黑狗,忽然停了下来。摇晃着硕大的狗头,竖起了耳朵。不安的撮了撮鼻子,嗅着周围的空气,发出一阵粗闷的鼻息。二叔心里一紧,摸了摸那狗头。黑狗伸出舌头舔了舔二叔的手,不声不响地晃动着尾巴。二叔做了一个手势,大黑狗眦出了白森森的牙刀,伏低身子,慢慢地向前摸去。
转过弯来,大黑狗就在不远处,静静的卧着,无声的耸动着脸毛。二叔和三个伙伴,也随后赶了过来。几支手电照在了地上,大伙儿直瞧得脸色苍白,谁也作声不得。
地上扔着一把猎枪,那是县里有名儿的老猎人——七爷的心爱之物,枪身上却沾满了鲜血。二叔慢慢弯下腰,伸手去拾,那血,还没有全干!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句俗语:“枪在人在”的隐意。七爷如果还活着,断不会丢下这把猎枪。
二叔转脸问那几个同伴:“现在是回去,还是继续搜寻七爷?”一个后生鼓足了勇气,对二叔说:“虎子哥,七爷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他老人家都折在了这里,咱们还是先撤回去吧。”二叔知道这几个人是怕了,二叔自己心里也是有些发毛。
大黑狗却站了起来,暴躁地朝前跑了两步,又转回身来。前肢搭在二叔的身上,舔着二叔的手,轻轻的吠叫着。二叔想了想,还是跟着大黑狗向前走去。几个同伴略略迟疑,也都跟了上来。
约摸走了能有十来分钟,大黑狗再一次掉转过身来,绕着二叔兜起了圈子。洞穴里不通风,二叔等人提鼻子一闻,都不禁皱了皱眉头。前面传来的,是一股异味,熏得人一阵阵的作呕。几个人互相看了看,二叔冲他们摆了摆手,他一个人秉住这口气,悄悄的摸了过去。
手电照去,那是血肉模糊的一堆,有骨有肉。几个后生大着胆子摸了上来,看了一会儿,有人忍不住问道:“虎子哥,这会不会是?” 二叔“哼”了一声:“就是那头猪,这是被吃剩的。”话音未落,有人失声道:“那玩意儿,难道就在这附近?”
大黑狗突然纵身跳起,抖动着耳朵,发出阵阵低沉的吠叫。狗眼里冒出来兽性的凶狠,四条腿直直地挺立着,急促的摇摇尾巴,眦出如同刀锋一样锐利的牙齿。那牙齿,白生生的,在黑暗中看得格外的瘆人。二叔吸了口冷气,变了脸色:“那玩意儿就在这,咱们现在,怕是走不得了。”
大黑狗焦急地狂吠,蹬直了粗壮的后腿,随时准备扑过去。二叔将心一横,打了一声口哨。大黑狗一窜老远,直没入了黑暗里。二叔回过头看定几个同伴,脸上的表情有几分狰狞:“要走,你们只管走。我今天,要拼个鱼死网破”。
二叔一个人往前走去。他不用回头也知道,背后没有人跟上。他苦笑了一下,心头并不恨怨,反倒轻松了。生死有命,在此一搏。忽地,前面传来大黑狗,疯狂的吼叫声。大黑狗凶悍的战斗力,二叔是深知的。前年春天,村里闹开了狼,把村里的羊,先后拖走了四、五只。大黑狗被激怒了,不声不响地一路追踪,和狼群碰了个正着。最终大黑狗以一抵七,狗肚子被咬开,肠子都拖出来了,还是硬生生地咬死了七头饿狼。但现在面对的,是那个未知生物,大黑狗又有多少胜算呢?
据说人如果豁出去了一切,就不会畏惧死亡了。二叔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五响翻子”,直接冲了上去。



你们听说过哪些关于黄河的奇闻异事,历史故事?葭明通来说一段江苏徐州丰县废黄河变果园的历史故事吧!这个戈壁滩是怎么来的呢?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大沙河。起码应该有很多会读书懂科学的人来做这些工作才好!普通的农民群众是做不来这种工作的。然后就到了1957年!一致认为在“大沙河”应该直接种果树,尤其苹果树,不用搞什么防护林然后再造良田种庄稼的,不划算。遗惠今日!起码!在那个特殊年代,丰县征服了废黄河“小戈壁滩”,可以类比大寨梯田!
那是一个清晨,二叔去黄河边,取昨天晚上下好的网。让他意外的是,网里一条鱼也没有。却有一个透明的,乒乓球大小的物体。二叔有些好奇,用手指戳戳,感觉粘乎乎的。放在鼻子下面闻闻,有一股腥臭味,差点吐出来。
二叔很恼火,想把这个球状生物给扔了。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因为这个球状生物是活的,会扭来扭去。身体一会儿圆,一会儿扁,一会儿条。二叔看着有趣,就留了下来。
家中有个空置的水缸,二叔往里面倒了多半缸水,就把球状生物养在了里面。也许是怕太突兀了,还扔了五、六尾鲤鱼在里面。
二叔要忙去农活,一直到天擦黑,才回到了家里。想着早上捞的球状生物,便来到了水缸前。这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当真是吓了一跳。缸里的水,一片殷红。那生物倒还在缸里,只不过,已经变得有碗口那么大。缸里的五、六尾鲤鱼却只剩下了骨架,沉在了缸底。
二叔有些吃惊。这玩意儿,还能吃活鱼?他想了想,去厨下又捞了尾鲤鱼,投入了缸里。鲤鱼入缸,自由自在的游动着。没过多久,那个碗口大的生物,慢慢凑了过来,一下子便贴在了鲤鱼的身上。那鲤鱼拼命摆动,哪里挣脱的开?也就是眨眼睛的工夫,就被吞噬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缸里的水更是一片血红。
二叔倒抽了口冷气,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时,院里的长辈叫他去吃晚饭,他就暂时把这事儿给搁下了。等二叔再次想到这球状生物,已是第二天的晌午了。不知怎地,他心里有些发毛,人来到缸前,不禁又大吃一惊!
缸里只残留了一个篮球大小的透明膜儿,从中间撕裂了一个大洞,倒像是蜕下的皮。这玩意儿难道是跑了?二叔挠了挠头,在院里搜寻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也只好作罢了。
过了三、五天,二叔就把这事儿抛在了脑后。直到他有天傍晚收工回来,见邻居老王家门口,围了一大圈人。原来是老王媳妇儿站在门外“骂大街”,他才觉得是出了祸事!
老王家里,养了多年的一条黄狗。不吱声不吱气的,被吃得只剩下了骨架。老王媳妇儿那是一个泼辣女人,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这才站在自家门前破口大骂。二叔挤进了人群,看见了地上的黄狗骨架,打了个冷战。心头突突的乱跳,张嘴想说些什么,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二叔低着头,进了家门,他的心里很乱。第一,他不能确定,吃掉黄狗的,就是那个玩意儿。第二,就算说出来了,村里会有人信吗?第三,那玩意儿是他带回村里的,吃了一条黄狗事小,那老王媳妇儿却是出了名的泼辣货,二叔怎敢平白招惹?
一晃又过了几天,村子里风平浪静,什么事儿都没出。二叔松了一口气,暗暗庆幸自己沉得住气,没有吐露出别的。
事情就出在这天的上半夜。周家的小媳妇儿,爬起来给“大牲口棚”的牛、马添喂草料。她喂了一圈,独独不见家里那头健硕的水牛“老黑”。心头好生疑惑,这水牛能去哪里?又听得棚里隐约有些声响,便举着“煤油灯”细细看去。只见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水牛倒伏在角落,早没了气。大半边身子只剩下了森森白骨,一大团黑乎乎的的东西,将“老黑”紧紧裹住,还在不住的吞噬。周家小媳妇儿的那声尖叫:带着惶恐,带着愤怒,带着绝望。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几十年都过去了,原来谁也不曾忘却。
最先赶来的是周家的几个男人,他们看到了瘫倒在地上,崩溃的小媳妇儿。也看到了“牲口棚”里的可怕场景:那头水牛,只剩下小半段还有肉,大部分都成了骨架。但是吞噬水牛的东西,却没有了踪影。周家的人,脸都绿了,身子抖的厉害,就这么僵立着不动。村里人先后赶了过来,因为担心碰上了贼或者是野兽,不少男人手上还操着锄头、铁铲、木棒。
二叔也在人群当中,他的脸色苍白,如果不是手里握有一根木棒,都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等弄明白出了什么事,村民们面面相觑,一时没了主张,谁也不敢乱说话。
二叔大着胆子走进了“牲口棚”,举着“煤油灯”,里外又照了好一通。老周头看向他,紧张的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虎子,怎,怎么了?”二叔用木棒在地面戳了几下:“那东西,就藏在地里面”。
十几把锄头,铁铲在棚里挖了起来。挖了约摸半支烟的光景,村民们不再动手了,几十双眼睛,直勾勾 盯着翻挖出的泥土。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泥土上,沾染着大片大片鲜红的液体。村里的屠户用颤抖着的手沾了一点,只闻了闻,就变了脸色:“是牛血!”
二叔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睁开。他咬紧牙关,做了一个手势。村民们略略犹豫,便又挖了起来,约摸挖了十来分钟,村民们再次住了手。眼前的深坑里,有一大团鱼网状、深黑色的薄膜。如果完全铺展开来,那个面积怕是能覆盖住一头大象。二叔的头都大了,前后不过十来天,那玩意儿竟然生长得如此之大!
夜幕下,在村里的一处空旷所在,村民们牢牢地绑好了一口肥猪,估摸着也有二百多斤。屠户看准时机,在猪的喉咙上一刀刺入,伤口并不太深,那猪不断惨叫,鲜血汩汩地淌着。做好这一切,村民们各自寻好隐匿之处,埋伏起来静静的候着。
每个村民心中都忐忑不安,也不知等了多久,眼见得周围黑沉沉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鸟鸣。西北角的一株老树上,藏定一人,却是县里有名的老猎手。他伏在粗大的树干上,汗水自额头慢慢的渗出,他却一动也不动,只是用力紧握着那把猎枪。
二叔和老周家的,秉住了呼吸,各自蹲守在一口大水缸里。那大缸摆放在肥猪的两侧,双方相距不过两、三米远,每人手里都是一枝“五响翻子”。肥猪咽喉处的伤口越痛,便越挣扎。而肥猪越挣扎,血淌的便更多。不得不说,人是万物之灵。二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待那话儿现身,便打得它满身都是血窟窿眼。
蓦地,二叔只觉得脚下的大地,剧烈的抖动了起来。他小心翼翼的揭开缸盖,发现不远处鼓起了一个极大的土包,正一点一点的向肥猪的方向慢慢推进。他心里一紧,暗暗思量:终于等到你了!
土包的顶端,却在不停的蠕动着,分明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二叔长长的吐了口气,慢慢将手里的“五响翻子”对准了前方,手指因为紧张,微微有些发颤。他死命咬住下唇,都咬出血来了,这才稳住心神。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响,土包猛地翻了开来。二叔只瞧了一眼,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从缸里蹦出来。那土里冒出来的,竟然是成千上万只,又肥又大的灰毛老鼠!这老鼠群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便铺满了整个儿大地,疯狂的到处乱跑、乱钻。埋伏在四周的村民,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发一声喊,硬着头皮举起手中的锄头、铁铲奋力拍打。最奇的是,那些老鼠见了人,不但不怕,反而争先恐后的窜上身来,张口便咬。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眼见得数十个青壮年,人人身上都爬挂了无数只老鼠。村民们立刻乱了阵脚,有人实在撑不住了,撒开双腿,掉头往家中就跑。
树上的老猎人,对着躁动着的“鼠海”连连开了五、六枪,轰翻了一大片!但枪声、火药味儿,同类血肉模糊的尸体,受伤后翻滚挣扎的惨叫,一点儿也没有震慑到鼠群。老鼠们就像是疯了,完全是不管不顾的架式。二叔心里知道:完了!这混乱的局面,对村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他并不知道,这才刚刚拉开了序幕,真正的灭顶之灾还在后头呢。
二叔才窜出水缸,就遭到了几十只灰毛老鼠的疯狂撕咬,不到一分钟,身上就多处挂彩。他揩去脸上的血渍,飞快的打了声呼哨,一条黑狗便从不远处的灌木丛里窜出来。那黑狗体型巨大,好似牛犊大小,一看就知道非同寻常。二叔左手拍打着身上的老鼠,右手往鼠群一指,怒吼道:“老怪!给我狠狠的咬!”
黑狗的喉咙里发出炸雷似的声音,好不吓人!它准确的领会了主人的指令,从二叔身边一掠而过,箭一般迎着鼠群扑了上去。黑狗张开巨口,利如锋刃的狗牙横切竖割,草丛里,泥土里,黑狗的皮毛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攻击,鼠群起先是溃败的,但很快就开始了全面反击。黑狗即便再凶悍,面对成千上万的灰毛老鼠,也是绝无胜算!很快,狗血从浑身的十几个裂口中冒了出来,像是一条条小溪在无声的流淌。
但黑狗的战斗力是可怕的,竟然完全不在乎身上的伤势,仍在鼠群里左突右闯,前冲后撞,疯狂扑咬。这给了二叔一个机会。他跌跌撞撞,一头抢进了附近的一间“仓房”。那里摆放着木头、砖瓦、铁铲、锄头、马灯、煤油箱等杂物。他三两下扎好了一只“火把”,淋上了煤油,随手点燃,便冲了出来。
二叔咬牙切齿,手持“火把”,一步一步迎着鼠群走了过去。这一招极为有效,鼠群立时大乱。那老鼠见了火,如何不怕?纷纷退后,却不逃散,只围着“火把”团团打着转。二叔心里有数,胆子也更壮了,抢行几步,逼得鼠群又往后退了一段!口中大声喝道:“老周家的,叫上几个人,快去把村里的猫儿都赶过来!”
老周家的应了一声,撒腿就跑。在这乡下,家家几乎都养着猫儿避鼠的。天到这般时候,那些猫儿大多聚在一起,在茅屋外四下里游荡。二叔手中的“火把”此时虽旺,但鼠群似乎也明白,这火终会燃尽,并不远避。二叔心头焦躁,只盼着猫儿早些出来解困。忽见老周家的,抱着一只肥大的狸花猫,身后跟着五、六十个后生,每人怀里都抱着只猫儿,匆匆的赶了过来。
二叔心头,大喜过望。这猫和老鼠,是与生俱来的天敌。但凡是碰上了,必是要斗个不死不休。乡下的狸花猫,捕鼠更是能手。果然,那狸花猫看到老鼠,眼睛瞪得又大又圆。身上的毛倒竖起来,不待主人吩咐,喵的一声,便纵身一跃,扑了上去。这狸花猫实在是厉害,一口气便咬翻了数十只老鼠!那些个猫儿,见了老鼠,也都来了精神,一只接一只相继扑了上去,到处追咬。正在恶斗中的黑狗红了眼,它对身上的伤口已经麻木了。负了伤的黑狗没眨一下眼睛,就发动了新的进攻,必要置鼠群于死地。看准时机,黑狗发出一声声炸雷般的猛吼,化作黑色的旋风,朝前猛扑,又是一通死命撕咬。那鼠群虽说成千上万,但见了天敌,先自慌了。二叔和后生们,又先后点起了数十枝“火把”。鼠群再也扛不住了,四散奔逃,转眼间便逃得干干净净。
村民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过神来,看着满地血肉模糊的灰毛老鼠尸体,当真令人阵阵作呕,有些人更是张嘴吐了起来。二叔转脸,向那口肥猪的所在看去,不觉一怔,那头肥猪竟然不见了!二叔心里一慌,急忙奔到近前。方才只顾着和鼠群大战,地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大洞,黑洞洞的也不知深浅,那猪定是被拖入了洞穴深处。
二叔正犯着寻思,忽听得有人高喊道:“七爷,七爷怎么不见了?”那七爷便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一直藏身于西北角的老树上。好端端的,怎会不见了踪影?二叔找了一支手电,向下细细照去。赫然发现一只“长烟管”,正是七爷的心爱之物。想来,七爷定是看到肥猪被拖入了洞穴,他艺高人胆大,竟然也钻了进去。这时,有一些村民,也看出了情势不对,围了过来。
二叔把自己的推断,对众人简单的说了一下。便要带着黑狗下到洞穴,去接应七爷。众人哪肯让二叔一个人去犯险?当下选出来五、六个后生,人手一枝“五响翻子”,要陪着二叔一起探洞穴。
二叔打了个手势,黑狗便钻进了洞穴。二叔和那些后生,各自打着手电,紧紧地跟在黑狗的后面。那洞穴深处,却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虽然人人都拿着手电,也只不过能照亮前方两米的距离,再远的地方,那便是无尽的黑暗。
人在黑暗中行走,因为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心里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为防止发生意外,二叔特地又交代了一番。几个人在洞里走了几分钟后,大家的“方向感”就全没了。二叔倒不是太在意,只要有大黑狗在,这些都不算事儿。
走在队伍最后的,是一个叫大春的。他性子最是鲁莽,二叔怕他添乱,所以有意把他压在了队尾。说起来,大春是喝凉水塞牙缝,倒霉透了。在上个转弯处,他不小心崴脚了。按理来说,他应该立刻呼叫前面的队伍,但他为人过于好胜要强,暗暗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拖着右腿努力跟上。
又走了一段,大春的右腿脚踝处疼的越发厉害了。他用手电一照,自己也吓了一跳,那里肿的像是个馒头。他知道没法再跟下去,便对着前面大声喊着我二叔的名字:“虎子,虎子”。
二叔听见了,立刻摆手示意队伍停止前进,原地不动。大黑狗挺直了四腿,尾巴轻轻的晃了一下,在黑暗中的那双狗眼,闪闪发光。二叔拍了拍巨大的狗头,一个人向后找了过来。等两个人碰了面,二叔弄清了原委,又看了看大春的脚踝,耽搁不得。二叔当即决定,叫来一个后生,扶着大春原路返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后生搀扶着大春,打着手电慢慢的顺着来路往回走。才走了两个转弯口,大春就发现了问题,这路不对。周围实在是太黑了,两支手电筒照向远处,还是瞧得不太明白。大春黑着脸告诉后生:“我们方向走错了,这条路,我们压根没走过。”
后生是一脸懵逼。大春心里也觉得纳闷。这人下了洞穴,才走了多远?况且一路上,也没有看到有岔道啊。两人正犯着寻思,忽听得前方黑暗里,隐约传来几声狗吠。虽然听得不是很清,但大春和后生还是听出来了,是那只大黑狗发出的。
两人不禁呆了一呆。这是闹哪一出啊?怎么又绕到虎子那些人的前面来了?大春和后生想了想,还是打着手电,向着声音的方向摸了过去。
又走了好一段路,那狗吠声仍然是忽远忽近,飘忽不定,似是在引领着大春和后生。大春心里有些起疑,便站定了,不肯再往前去。后生的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安,在旁边悄声的说道:“大春哥,走了老半天了,那狗倒底在哪呢?要不,咱们喊两声试试?”
过了一会,大春轻声说道:“把手电都灭了”。后生微微一怔,随即照做了。四周顿时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大春又拉了拉后生的手,两人慢慢伏下身子。后生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这心跳得好厉害,和打鼓一般。
前面的黑暗处,又隐约传来了一些动静,但这次不是狗吠。大春慢慢用胳膊撞了撞身旁的后生,那人会意,两枝“五响翻子”同时顺过了枪管。又过了分把钟,只听得前面动静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仔细分辩,似乎是什么东西喘息的声音,好生的怪异。大春猛地打亮了手电,向前方照了过去。这手电的光亮并不好,但因为离的太近,大春和后生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大春那晚死在了当场,后生却侥幸活了下来,只是变成了疯子。后生一直到死,大伙儿在他嘴里,唯一听得明白的一句话是:“真的有鬼。”
走在最前面的大黑狗,忽然停了下来。摇晃着硕大的狗头,竖起了耳朵。不安的撮了撮鼻子,嗅着周围的空气,发出一阵粗闷的鼻息。二叔心里一紧,摸了摸那狗头。黑狗伸出舌头舔了舔二叔的手,不声不响地晃动着尾巴。二叔做了一个手势,大黑狗眦出了白森森的牙刀,伏低身子,慢慢地向前摸去。
转过弯来,大黑狗就在不远处,静静的卧着,无声的耸动着脸毛。二叔和三个伙伴,也随后赶了过来。几支手电照在了地上,大伙儿直瞧得脸色苍白,谁也作声不得。
地上扔着一把猎枪,那是县里有名儿的老猎人——七爷的心爱之物,枪身上却沾满了鲜血。二叔慢慢弯下腰,伸手去拾,那血,还没有全干!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句俗语:“枪在人在”的隐意。七爷如果还活着,断不会丢下这把猎枪。
二叔转脸问那几个同伴:“现在是回去,还是继续搜寻七爷?”一个后生鼓足了勇气,对二叔说:“虎子哥,七爷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他老人家都折在了这里,咱们还是先撤回去吧。”二叔知道这几个人是怕了,二叔自己心里也是有些发毛。
大黑狗却站了起来,暴躁地朝前跑了两步,又转回身来。前肢搭在二叔的身上,舔着二叔的手,轻轻的吠叫着。二叔想了想,还是跟着大黑狗向前走去。几个同伴略略迟疑,也都跟了上来。
约摸走了能有十来分钟,大黑狗再一次掉转过身来,绕着二叔兜起了圈子。洞穴里不通风,二叔等人提鼻子一闻,都不禁皱了皱眉头。前面传来的,是一股异味,熏得人一阵阵的作呕。几个人互相看了看,二叔冲他们摆了摆手,他一个人秉住这口气,悄悄的摸了过去。
手电照去,那是血肉模糊的一堆,有骨有肉。几个后生大着胆子摸了上来,看了一会儿,有人忍不住问道:“虎子哥,这会不会是?” 二叔“哼”了一声:“就是那头猪,这是被吃剩的。”话音未落,有人失声道:“那玩意儿,难道就在这附近?”
大黑狗突然纵身跳起,抖动着耳朵,发出阵阵低沉的吠叫。狗眼里冒出来兽性的凶狠,四条腿直直地挺立着,急促的摇摇尾巴,眦出如同刀锋一样锐利的牙齿。那牙齿,白生生的,在黑暗中看得格外的瘆人。二叔吸了口冷气,变了脸色:“那玩意儿就在这,咱们现在,怕是走不得了。”
大黑狗焦急地狂吠,蹬直了粗壮的后腿,随时准备扑过去。二叔将心一横,打了一声口哨。大黑狗一窜老远,直没入了黑暗里。二叔回过头看定几个同伴,脸上的表情有几分狰狞:“要走,你们只管走。我今天,要拼个鱼死网破”。
二叔一个人往前走去。他不用回头也知道,背后没有人跟上。他苦笑了一下,心头并不恨怨,反倒轻松了。生死有命,在此一搏。忽地,前面传来大黑狗,疯狂的吼叫声。大黑狗凶悍的战斗力,二叔是深知的。前年春天,村里闹开了狼,把村里的羊,先后拖走了四、五只。大黑狗被激怒了,不声不响地一路追踪,和狼群碰了个正着。最终大黑狗以一抵七,狗肚子被咬开,肠子都拖出来了,还是硬生生地咬死了七头饿狼。但现在面对的,是那个未知生物,大黑狗又有多少胜算呢?
据说人如果豁出去了一切,就不会畏惧死亡了。二叔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五响翻子”,直接冲了上去。



你们听说过哪些关于黄河的奇闻异事,历史故事?葭明通来说一段江苏徐州丰县废黄河变果园的历史故事吧!这个戈壁滩是怎么来的呢?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大沙河。起码应该有很多会读书懂科学的人来做这些工作才好!普通的农民群众是做不来这种工作的。然后就到了1957年!一致认为在“大沙河”应该直接种果树,尤其苹果树,不用搞什么防护林然后再造良田种庄稼的,不划算。遗惠今日!起码!在那个特殊年代,丰县征服了废黄河“小戈壁滩”,可以类比大寨梯田!
那是一个清晨,二叔去黄河边,取昨天晚上下好的网。让他意外的是,网里一条鱼也没有。却有一个透明的,乒乓球大小的物体。二叔有些好奇,用手指戳戳,感觉粘乎乎的。放在鼻子下面闻闻,有一股腥臭味,差点吐出来。
二叔很恼火,想把这个球状生物给扔了。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因为这个球状生物是活的,会扭来扭去。身体一会儿圆,一会儿扁,一会儿条。二叔看着有趣,就留了下来。
家中有个空置的水缸,二叔往里面倒了多半缸水,就把球状生物养在了里面。也许是怕太突兀了,还扔了五、六尾鲤鱼在里面。
二叔要忙去农活,一直到天擦黑,才回到了家里。想着早上捞的球状生物,便来到了水缸前。这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当真是吓了一跳。缸里的水,一片殷红。那生物倒还在缸里,只不过,已经变得有碗口那么大。缸里的五、六尾鲤鱼却只剩下了骨架,沉在了缸底。
二叔有些吃惊。这玩意儿,还能吃活鱼?他想了想,去厨下又捞了尾鲤鱼,投入了缸里。鲤鱼入缸,自由自在的游动着。没过多久,那个碗口大的生物,慢慢凑了过来,一下子便贴在了鲤鱼的身上。那鲤鱼拼命摆动,哪里挣脱的开?也就是眨眼睛的工夫,就被吞噬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缸里的水更是一片血红。
二叔倒抽了口冷气,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时,院里的长辈叫他去吃晚饭,他就暂时把这事儿给搁下了。等二叔再次想到这球状生物,已是第二天的晌午了。不知怎地,他心里有些发毛,人来到缸前,不禁又大吃一惊!
缸里只残留了一个篮球大小的透明膜儿,从中间撕裂了一个大洞,倒像是蜕下的皮。这玩意儿难道是跑了?二叔挠了挠头,在院里搜寻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也只好作罢了。
过了三、五天,二叔就把这事儿抛在了脑后。直到他有天傍晚收工回来,见邻居老王家门口,围了一大圈人。原来是老王媳妇儿站在门外“骂大街”,他才觉得是出了祸事!
老王家里,养了多年的一条黄狗。不吱声不吱气的,被吃得只剩下了骨架。老王媳妇儿那是一个泼辣女人,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这才站在自家门前破口大骂。二叔挤进了人群,看见了地上的黄狗骨架,打了个冷战。心头突突的乱跳,张嘴想说些什么,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二叔低着头,进了家门,他的心里很乱。第一,他不能确定,吃掉黄狗的,就是那个玩意儿。第二,就算说出来了,村里会有人信吗?第三,那玩意儿是他带回村里的,吃了一条黄狗事小,那老王媳妇儿却是出了名的泼辣货,二叔怎敢平白招惹?
一晃又过了几天,村子里风平浪静,什么事儿都没出。二叔松了一口气,暗暗庆幸自己沉得住气,没有吐露出别的。
事情就出在这天的上半夜。周家的小媳妇儿,爬起来给“大牲口棚”的牛、马添喂草料。她喂了一圈,独独不见家里那头健硕的水牛“老黑”。心头好生疑惑,这水牛能去哪里?又听得棚里隐约有些声响,便举着“煤油灯”细细看去。只见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水牛倒伏在角落,早没了气。大半边身子只剩下了森森白骨,一大团黑乎乎的的东西,将“老黑”紧紧裹住,还在不住的吞噬。周家小媳妇儿的那声尖叫:带着惶恐,带着愤怒,带着绝望。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几十年都过去了,原来谁也不曾忘却。
最先赶来的是周家的几个男人,他们看到了瘫倒在地上,崩溃的小媳妇儿。也看到了“牲口棚”里的可怕场景:那头水牛,只剩下小半段还有肉,大部分都成了骨架。但是吞噬水牛的东西,却没有了踪影。周家的人,脸都绿了,身子抖的厉害,就这么僵立着不动。村里人先后赶了过来,因为担心碰上了贼或者是野兽,不少男人手上还操着锄头、铁铲、木棒。
二叔也在人群当中,他的脸色苍白,如果不是手里握有一根木棒,都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等弄明白出了什么事,村民们面面相觑,一时没了主张,谁也不敢乱说话。
二叔大着胆子走进了“牲口棚”,举着“煤油灯”,里外又照了好一通。老周头看向他,紧张的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虎子,怎,怎么了?”二叔用木棒在地面戳了几下:“那东西,就藏在地里面”。
十几把锄头,铁铲在棚里挖了起来。挖了约摸半支烟的光景,村民们不再动手了,几十双眼睛,直勾勾 盯着翻挖出的泥土。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泥土上,沾染着大片大片鲜红的液体。村里的屠户用颤抖着的手沾了一点,只闻了闻,就变了脸色:“是牛血!”
二叔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睁开。他咬紧牙关,做了一个手势。村民们略略犹豫,便又挖了起来,约摸挖了十来分钟,村民们再次住了手。眼前的深坑里,有一大团鱼网状、深黑色的薄膜。如果完全铺展开来,那个面积怕是能覆盖住一头大象。二叔的头都大了,前后不过十来天,那玩意儿竟然生长得如此之大!
夜幕下,在村里的一处空旷所在,村民们牢牢地绑好了一口肥猪,估摸着也有二百多斤。屠户看准时机,在猪的喉咙上一刀刺入,伤口并不太深,那猪不断惨叫,鲜血汩汩地淌着。做好这一切,村民们各自寻好隐匿之处,埋伏起来静静的候着。
每个村民心中都忐忑不安,也不知等了多久,眼见得周围黑沉沉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鸟鸣。西北角的一株老树上,藏定一人,却是县里有名的老猎手。他伏在粗大的树干上,汗水自额头慢慢的渗出,他却一动也不动,只是用力紧握着那把猎枪。
二叔和老周家的,秉住了呼吸,各自蹲守在一口大水缸里。那大缸摆放在肥猪的两侧,双方相距不过两、三米远,每人手里都是一枝“五响翻子”。肥猪咽喉处的伤口越痛,便越挣扎。而肥猪越挣扎,血淌的便更多。不得不说,人是万物之灵。二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待那话儿现身,便打得它满身都是血窟窿眼。
蓦地,二叔只觉得脚下的大地,剧烈的抖动了起来。他小心翼翼的揭开缸盖,发现不远处鼓起了一个极大的土包,正一点一点的向肥猪的方向慢慢推进。他心里一紧,暗暗思量:终于等到你了!
土包的顶端,却在不停的蠕动着,分明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二叔长长的吐了口气,慢慢将手里的“五响翻子”对准了前方,手指因为紧张,微微有些发颤。他死命咬住下唇,都咬出血来了,这才稳住心神。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响,土包猛地翻了开来。二叔只瞧了一眼,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从缸里蹦出来。那土里冒出来的,竟然是成千上万只,又肥又大的灰毛老鼠!这老鼠群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便铺满了整个儿大地,疯狂的到处乱跑、乱钻。埋伏在四周的村民,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发一声喊,硬着头皮举起手中的锄头、铁铲奋力拍打。最奇的是,那些老鼠见了人,不但不怕,反而争先恐后的窜上身来,张口便咬。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眼见得数十个青壮年,人人身上都爬挂了无数只老鼠。村民们立刻乱了阵脚,有人实在撑不住了,撒开双腿,掉头往家中就跑。
树上的老猎人,对着躁动着的“鼠海”连连开了五、六枪,轰翻了一大片!但枪声、火药味儿,同类血肉模糊的尸体,受伤后翻滚挣扎的惨叫,一点儿也没有震慑到鼠群。老鼠们就像是疯了,完全是不管不顾的架式。二叔心里知道:完了!这混乱的局面,对村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他并不知道,这才刚刚拉开了序幕,真正的灭顶之灾还在后头呢。
二叔才窜出水缸,就遭到了几十只灰毛老鼠的疯狂撕咬,不到一分钟,身上就多处挂彩。他揩去脸上的血渍,飞快的打了声呼哨,一条黑狗便从不远处的灌木丛里窜出来。那黑狗体型巨大,好似牛犊大小,一看就知道非同寻常。二叔左手拍打着身上的老鼠,右手往鼠群一指,怒吼道:“老怪!给我狠狠的咬!”
黑狗的喉咙里发出炸雷似的声音,好不吓人!它准确的领会了主人的指令,从二叔身边一掠而过,箭一般迎着鼠群扑了上去。黑狗张开巨口,利如锋刃的狗牙横切竖割,草丛里,泥土里,黑狗的皮毛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攻击,鼠群起先是溃败的,但很快就开始了全面反击。黑狗即便再凶悍,面对成千上万的灰毛老鼠,也是绝无胜算!很快,狗血从浑身的十几个裂口中冒了出来,像是一条条小溪在无声的流淌。
但黑狗的战斗力是可怕的,竟然完全不在乎身上的伤势,仍在鼠群里左突右闯,前冲后撞,疯狂扑咬。这给了二叔一个机会。他跌跌撞撞,一头抢进了附近的一间“仓房”。那里摆放着木头、砖瓦、铁铲、锄头、马灯、煤油箱等杂物。他三两下扎好了一只“火把”,淋上了煤油,随手点燃,便冲了出来。
二叔咬牙切齿,手持“火把”,一步一步迎着鼠群走了过去。这一招极为有效,鼠群立时大乱。那老鼠见了火,如何不怕?纷纷退后,却不逃散,只围着“火把”团团打着转。二叔心里有数,胆子也更壮了,抢行几步,逼得鼠群又往后退了一段!口中大声喝道:“老周家的,叫上几个人,快去把村里的猫儿都赶过来!”
老周家的应了一声,撒腿就跑。在这乡下,家家几乎都养着猫儿避鼠的。天到这般时候,那些猫儿大多聚在一起,在茅屋外四下里游荡。二叔手中的“火把”此时虽旺,但鼠群似乎也明白,这火终会燃尽,并不远避。二叔心头焦躁,只盼着猫儿早些出来解困。忽见老周家的,抱着一只肥大的狸花猫,身后跟着五、六十个后生,每人怀里都抱着只猫儿,匆匆的赶了过来。
二叔心头,大喜过望。这猫和老鼠,是与生俱来的天敌。但凡是碰上了,必是要斗个不死不休。乡下的狸花猫,捕鼠更是能手。果然,那狸花猫看到老鼠,眼睛瞪得又大又圆。身上的毛倒竖起来,不待主人吩咐,喵的一声,便纵身一跃,扑了上去。这狸花猫实在是厉害,一口气便咬翻了数十只老鼠!那些个猫儿,见了老鼠,也都来了精神,一只接一只相继扑了上去,到处追咬。正在恶斗中的黑狗红了眼,它对身上的伤口已经麻木了。负了伤的黑狗没眨一下眼睛,就发动了新的进攻,必要置鼠群于死地。看准时机,黑狗发出一声声炸雷般的猛吼,化作黑色的旋风,朝前猛扑,又是一通死命撕咬。那鼠群虽说成千上万,但见了天敌,先自慌了。二叔和后生们,又先后点起了数十枝“火把”。鼠群再也扛不住了,四散奔逃,转眼间便逃得干干净净。
村民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过神来,看着满地血肉模糊的灰毛老鼠尸体,当真令人阵阵作呕,有些人更是张嘴吐了起来。二叔转脸,向那口肥猪的所在看去,不觉一怔,那头肥猪竟然不见了!二叔心里一慌,急忙奔到近前。方才只顾着和鼠群大战,地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大洞,黑洞洞的也不知深浅,那猪定是被拖入了洞穴深处。
二叔正犯着寻思,忽听得有人高喊道:“七爷,七爷怎么不见了?”那七爷便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一直藏身于西北角的老树上。好端端的,怎会不见了踪影?二叔找了一支手电,向下细细照去。赫然发现一只“长烟管”,正是七爷的心爱之物。想来,七爷定是看到肥猪被拖入了洞穴,他艺高人胆大,竟然也钻了进去。这时,有一些村民,也看出了情势不对,围了过来。
二叔把自己的推断,对众人简单的说了一下。便要带着黑狗下到洞穴,去接应七爷。众人哪肯让二叔一个人去犯险?当下选出来五、六个后生,人手一枝“五响翻子”,要陪着二叔一起探洞穴。
二叔打了个手势,黑狗便钻进了洞穴。二叔和那些后生,各自打着手电,紧紧地跟在黑狗的后面。那洞穴深处,却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虽然人人都拿着手电,也只不过能照亮前方两米的距离,再远的地方,那便是无尽的黑暗。
人在黑暗中行走,因为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心里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为防止发生意外,二叔特地又交代了一番。几个人在洞里走了几分钟后,大家的“方向感”就全没了。二叔倒不是太在意,只要有大黑狗在,这些都不算事儿。
走在队伍最后的,是一个叫大春的。他性子最是鲁莽,二叔怕他添乱,所以有意把他压在了队尾。说起来,大春是喝凉水塞牙缝,倒霉透了。在上个转弯处,他不小心崴脚了。按理来说,他应该立刻呼叫前面的队伍,但他为人过于好胜要强,暗暗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拖着右腿努力跟上。
又走了一段,大春的右腿脚踝处疼的越发厉害了。他用手电一照,自己也吓了一跳,那里肿的像是个馒头。他知道没法再跟下去,便对着前面大声喊着我二叔的名字:“虎子,虎子”。
二叔听见了,立刻摆手示意队伍停止前进,原地不动。大黑狗挺直了四腿,尾巴轻轻的晃了一下,在黑暗中的那双狗眼,闪闪发光。二叔拍了拍巨大的狗头,一个人向后找了过来。等两个人碰了面,二叔弄清了原委,又看了看大春的脚踝,耽搁不得。二叔当即决定,叫来一个后生,扶着大春原路返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后生搀扶着大春,打着手电慢慢的顺着来路往回走。才走了两个转弯口,大春就发现了问题,这路不对。周围实在是太黑了,两支手电筒照向远处,还是瞧得不太明白。大春黑着脸告诉后生:“我们方向走错了,这条路,我们压根没走过。”
后生是一脸懵逼。大春心里也觉得纳闷。这人下了洞穴,才走了多远?况且一路上,也没有看到有岔道啊。两人正犯着寻思,忽听得前方黑暗里,隐约传来几声狗吠。虽然听得不是很清,但大春和后生还是听出来了,是那只大黑狗发出的。
两人不禁呆了一呆。这是闹哪一出啊?怎么又绕到虎子那些人的前面来了?大春和后生想了想,还是打着手电,向着声音的方向摸了过去。
又走了好一段路,那狗吠声仍然是忽远忽近,飘忽不定,似是在引领着大春和后生。大春心里有些起疑,便站定了,不肯再往前去。后生的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安,在旁边悄声的说道:“大春哥,走了老半天了,那狗倒底在哪呢?要不,咱们喊两声试试?”
过了一会,大春轻声说道:“把手电都灭了”。后生微微一怔,随即照做了。四周顿时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大春又拉了拉后生的手,两人慢慢伏下身子。后生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这心跳得好厉害,和打鼓一般。
前面的黑暗处,又隐约传来了一些动静,但这次不是狗吠。大春慢慢用胳膊撞了撞身旁的后生,那人会意,两枝“五响翻子”同时顺过了枪管。又过了分把钟,只听得前面动静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仔细分辩,似乎是什么东西喘息的声音,好生的怪异。大春猛地打亮了手电,向前方照了过去。这手电的光亮并不好,但因为离的太近,大春和后生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大春那晚死在了当场,后生却侥幸活了下来,只是变成了疯子。后生一直到死,大伙儿在他嘴里,唯一听得明白的一句话是:“真的有鬼。”
走在最前面的大黑狗,忽然停了下来。摇晃着硕大的狗头,竖起了耳朵。不安的撮了撮鼻子,嗅着周围的空气,发出一阵粗闷的鼻息。二叔心里一紧,摸了摸那狗头。黑狗伸出舌头舔了舔二叔的手,不声不响地晃动着尾巴。二叔做了一个手势,大黑狗眦出了白森森的牙刀,伏低身子,慢慢地向前摸去。
转过弯来,大黑狗就在不远处,静静的卧着,无声的耸动着脸毛。二叔和三个伙伴,也随后赶了过来。几支手电照在了地上,大伙儿直瞧得脸色苍白,谁也作声不得。
地上扔着一把猎枪,那是县里有名儿的老猎人——七爷的心爱之物,枪身上却沾满了鲜血。二叔慢慢弯下腰,伸手去拾,那血,还没有全干!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句俗语:“枪在人在”的隐意。七爷如果还活着,断不会丢下这把猎枪。
二叔转脸问那几个同伴:“现在是回去,还是继续搜寻七爷?”一个后生鼓足了勇气,对二叔说:“虎子哥,七爷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他老人家都折在了这里,咱们还是先撤回去吧。”二叔知道这几个人是怕了,二叔自己心里也是有些发毛。
大黑狗却站了起来,暴躁地朝前跑了两步,又转回身来。前肢搭在二叔的身上,舔着二叔的手,轻轻的吠叫着。二叔想了想,还是跟着大黑狗向前走去。几个同伴略略迟疑,也都跟了上来。
约摸走了能有十来分钟,大黑狗再一次掉转过身来,绕着二叔兜起了圈子。洞穴里不通风,二叔等人提鼻子一闻,都不禁皱了皱眉头。前面传来的,是一股异味,熏得人一阵阵的作呕。几个人互相看了看,二叔冲他们摆了摆手,他一个人秉住这口气,悄悄的摸了过去。
手电照去,那是血肉模糊的一堆,有骨有肉。几个后生大着胆子摸了上来,看了一会儿,有人忍不住问道:“虎子哥,这会不会是?” 二叔“哼”了一声:“就是那头猪,这是被吃剩的。”话音未落,有人失声道:“那玩意儿,难道就在这附近?”
大黑狗突然纵身跳起,抖动着耳朵,发出阵阵低沉的吠叫。狗眼里冒出来兽性的凶狠,四条腿直直地挺立着,急促的摇摇尾巴,眦出如同刀锋一样锐利的牙齿。那牙齿,白生生的,在黑暗中看得格外的瘆人。二叔吸了口冷气,变了脸色:“那玩意儿就在这,咱们现在,怕是走不得了。”
大黑狗焦急地狂吠,蹬直了粗壮的后腿,随时准备扑过去。二叔将心一横,打了一声口哨。大黑狗一窜老远,直没入了黑暗里。二叔回过头看定几个同伴,脸上的表情有几分狰狞:“要走,你们只管走。我今天,要拼个鱼死网破”。
二叔一个人往前走去。他不用回头也知道,背后没有人跟上。他苦笑了一下,心头并不恨怨,反倒轻松了。生死有命,在此一搏。忽地,前面传来大黑狗,疯狂的吼叫声。大黑狗凶悍的战斗力,二叔是深知的。前年春天,村里闹开了狼,把村里的羊,先后拖走了四、五只。大黑狗被激怒了,不声不响地一路追踪,和狼群碰了个正着。最终大黑狗以一抵七,狗肚子被咬开,肠子都拖出来了,还是硬生生地咬死了七头饿狼。但现在面对的,是那个未知生物,大黑狗又有多少胜算呢?
据说人如果豁出去了一切,就不会畏惧死亡了。二叔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五响翻子”,直接冲了上去。



你们听说过哪些关于黄河的奇闻异事,历史故事?葭明通来说一段江苏徐州丰县废黄河变果园的历史故事吧!这个戈壁滩是怎么来的呢?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大沙河。起码应该有很多会读书懂科学的人来做这些工作才好!普通的农民群众是做不来这种工作的。然后就到了1957年!一致认为在“大沙河”应该直接种果树,尤其苹果树,不用搞什么防护林然后再造良田种庄稼的,不划算。遗惠今日!起码!在那个特殊年代,丰县征服了废黄河“小戈壁滩”,可以类比大寨梯田!
那是一个清晨,二叔去黄河边,取昨天晚上下好的网。让他意外的是,网里一条鱼也没有。却有一个透明的,乒乓球大小的物体。二叔有些好奇,用手指戳戳,感觉粘乎乎的。放在鼻子下面闻闻,有一股腥臭味,差点吐出来。
二叔很恼火,想把这个球状生物给扔了。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因为这个球状生物是活的,会扭来扭去。身体一会儿圆,一会儿扁,一会儿条。二叔看着有趣,就留了下来。
家中有个空置的水缸,二叔往里面倒了多半缸水,就把球状生物养在了里面。也许是怕太突兀了,还扔了五、六尾鲤鱼在里面。
二叔要忙去农活,一直到天擦黑,才回到了家里。想着早上捞的球状生物,便来到了水缸前。这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当真是吓了一跳。缸里的水,一片殷红。那生物倒还在缸里,只不过,已经变得有碗口那么大。缸里的五、六尾鲤鱼却只剩下了骨架,沉在了缸底。
二叔有些吃惊。这玩意儿,还能吃活鱼?他想了想,去厨下又捞了尾鲤鱼,投入了缸里。鲤鱼入缸,自由自在的游动着。没过多久,那个碗口大的生物,慢慢凑了过来,一下子便贴在了鲤鱼的身上。那鲤鱼拼命摆动,哪里挣脱的开?也就是眨眼睛的工夫,就被吞噬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缸里的水更是一片血红。
二叔倒抽了口冷气,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时,院里的长辈叫他去吃晚饭,他就暂时把这事儿给搁下了。等二叔再次想到这球状生物,已是第二天的晌午了。不知怎地,他心里有些发毛,人来到缸前,不禁又大吃一惊!
缸里只残留了一个篮球大小的透明膜儿,从中间撕裂了一个大洞,倒像是蜕下的皮。这玩意儿难道是跑了?二叔挠了挠头,在院里搜寻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也只好作罢了。
过了三、五天,二叔就把这事儿抛在了脑后。直到他有天傍晚收工回来,见邻居老王家门口,围了一大圈人。原来是老王媳妇儿站在门外“骂大街”,他才觉得是出了祸事!
老王家里,养了多年的一条黄狗。不吱声不吱气的,被吃得只剩下了骨架。老王媳妇儿那是一个泼辣女人,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这才站在自家门前破口大骂。二叔挤进了人群,看见了地上的黄狗骨架,打了个冷战。心头突突的乱跳,张嘴想说些什么,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二叔低着头,进了家门,他的心里很乱。第一,他不能确定,吃掉黄狗的,就是那个玩意儿。第二,就算说出来了,村里会有人信吗?第三,那玩意儿是他带回村里的,吃了一条黄狗事小,那老王媳妇儿却是出了名的泼辣货,二叔怎敢平白招惹?
一晃又过了几天,村子里风平浪静,什么事儿都没出。二叔松了一口气,暗暗庆幸自己沉得住气,没有吐露出别的。
事情就出在这天的上半夜。周家的小媳妇儿,爬起来给“大牲口棚”的牛、马添喂草料。她喂了一圈,独独不见家里那头健硕的水牛“老黑”。心头好生疑惑,这水牛能去哪里?又听得棚里隐约有些声响,便举着“煤油灯”细细看去。只见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水牛倒伏在角落,早没了气。大半边身子只剩下了森森白骨,一大团黑乎乎的的东西,将“老黑”紧紧裹住,还在不住的吞噬。周家小媳妇儿的那声尖叫:带着惶恐,带着愤怒,带着绝望。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几十年都过去了,原来谁也不曾忘却。
最先赶来的是周家的几个男人,他们看到了瘫倒在地上,崩溃的小媳妇儿。也看到了“牲口棚”里的可怕场景:那头水牛,只剩下小半段还有肉,大部分都成了骨架。但是吞噬水牛的东西,却没有了踪影。周家的人,脸都绿了,身子抖的厉害,就这么僵立着不动。村里人先后赶了过来,因为担心碰上了贼或者是野兽,不少男人手上还操着锄头、铁铲、木棒。
二叔也在人群当中,他的脸色苍白,如果不是手里握有一根木棒,都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等弄明白出了什么事,村民们面面相觑,一时没了主张,谁也不敢乱说话。
二叔大着胆子走进了“牲口棚”,举着“煤油灯”,里外又照了好一通。老周头看向他,紧张的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虎子,怎,怎么了?”二叔用木棒在地面戳了几下:“那东西,就藏在地里面”。
十几把锄头,铁铲在棚里挖了起来。挖了约摸半支烟的光景,村民们不再动手了,几十双眼睛,直勾勾 盯着翻挖出的泥土。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泥土上,沾染着大片大片鲜红的液体。村里的屠户用颤抖着的手沾了一点,只闻了闻,就变了脸色:“是牛血!”
二叔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睁开。他咬紧牙关,做了一个手势。村民们略略犹豫,便又挖了起来,约摸挖了十来分钟,村民们再次住了手。眼前的深坑里,有一大团鱼网状、深黑色的薄膜。如果完全铺展开来,那个面积怕是能覆盖住一头大象。二叔的头都大了,前后不过十来天,那玩意儿竟然生长得如此之大!
夜幕下,在村里的一处空旷所在,村民们牢牢地绑好了一口肥猪,估摸着也有二百多斤。屠户看准时机,在猪的喉咙上一刀刺入,伤口并不太深,那猪不断惨叫,鲜血汩汩地淌着。做好这一切,村民们各自寻好隐匿之处,埋伏起来静静的候着。
每个村民心中都忐忑不安,也不知等了多久,眼见得周围黑沉沉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鸟鸣。西北角的一株老树上,藏定一人,却是县里有名的老猎手。他伏在粗大的树干上,汗水自额头慢慢的渗出,他却一动也不动,只是用力紧握着那把猎枪。
二叔和老周家的,秉住了呼吸,各自蹲守在一口大水缸里。那大缸摆放在肥猪的两侧,双方相距不过两、三米远,每人手里都是一枝“五响翻子”。肥猪咽喉处的伤口越痛,便越挣扎。而肥猪越挣扎,血淌的便更多。不得不说,人是万物之灵。二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待那话儿现身,便打得它满身都是血窟窿眼。
蓦地,二叔只觉得脚下的大地,剧烈的抖动了起来。他小心翼翼的揭开缸盖,发现不远处鼓起了一个极大的土包,正一点一点的向肥猪的方向慢慢推进。他心里一紧,暗暗思量:终于等到你了!
土包的顶端,却在不停的蠕动着,分明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二叔长长的吐了口气,慢慢将手里的“五响翻子”对准了前方,手指因为紧张,微微有些发颤。他死命咬住下唇,都咬出血来了,这才稳住心神。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响,土包猛地翻了开来。二叔只瞧了一眼,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从缸里蹦出来。那土里冒出来的,竟然是成千上万只,又肥又大的灰毛老鼠!这老鼠群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便铺满了整个儿大地,疯狂的到处乱跑、乱钻。埋伏在四周的村民,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发一声喊,硬着头皮举起手中的锄头、铁铲奋力拍打。最奇的是,那些老鼠见了人,不但不怕,反而争先恐后的窜上身来,张口便咬。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眼见得数十个青壮年,人人身上都爬挂了无数只老鼠。村民们立刻乱了阵脚,有人实在撑不住了,撒开双腿,掉头往家中就跑。
树上的老猎人,对着躁动着的“鼠海”连连开了五、六枪,轰翻了一大片!但枪声、火药味儿,同类血肉模糊的尸体,受伤后翻滚挣扎的惨叫,一点儿也没有震慑到鼠群。老鼠们就像是疯了,完全是不管不顾的架式。二叔心里知道:完了!这混乱的局面,对村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他并不知道,这才刚刚拉开了序幕,真正的灭顶之灾还在后头呢。
二叔才窜出水缸,就遭到了几十只灰毛老鼠的疯狂撕咬,不到一分钟,身上就多处挂彩。他揩去脸上的血渍,飞快的打了声呼哨,一条黑狗便从不远处的灌木丛里窜出来。那黑狗体型巨大,好似牛犊大小,一看就知道非同寻常。二叔左手拍打着身上的老鼠,右手往鼠群一指,怒吼道:“老怪!给我狠狠的咬!”
黑狗的喉咙里发出炸雷似的声音,好不吓人!它准确的领会了主人的指令,从二叔身边一掠而过,箭一般迎着鼠群扑了上去。黑狗张开巨口,利如锋刃的狗牙横切竖割,草丛里,泥土里,黑狗的皮毛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攻击,鼠群起先是溃败的,但很快就开始了全面反击。黑狗即便再凶悍,面对成千上万的灰毛老鼠,也是绝无胜算!很快,狗血从浑身的十几个裂口中冒了出来,像是一条条小溪在无声的流淌。
但黑狗的战斗力是可怕的,竟然完全不在乎身上的伤势,仍在鼠群里左突右闯,前冲后撞,疯狂扑咬。这给了二叔一个机会。他跌跌撞撞,一头抢进了附近的一间“仓房”。那里摆放着木头、砖瓦、铁铲、锄头、马灯、煤油箱等杂物。他三两下扎好了一只“火把”,淋上了煤油,随手点燃,便冲了出来。
二叔咬牙切齿,手持“火把”,一步一步迎着鼠群走了过去。这一招极为有效,鼠群立时大乱。那老鼠见了火,如何不怕?纷纷退后,却不逃散,只围着“火把”团团打着转。二叔心里有数,胆子也更壮了,抢行几步,逼得鼠群又往后退了一段!口中大声喝道:“老周家的,叫上几个人,快去把村里的猫儿都赶过来!”
老周家的应了一声,撒腿就跑。在这乡下,家家几乎都养着猫儿避鼠的。天到这般时候,那些猫儿大多聚在一起,在茅屋外四下里游荡。二叔手中的“火把”此时虽旺,但鼠群似乎也明白,这火终会燃尽,并不远避。二叔心头焦躁,只盼着猫儿早些出来解困。忽见老周家的,抱着一只肥大的狸花猫,身后跟着五、六十个后生,每人怀里都抱着只猫儿,匆匆的赶了过来。
二叔心头,大喜过望。这猫和老鼠,是与生俱来的天敌。但凡是碰上了,必是要斗个不死不休。乡下的狸花猫,捕鼠更是能手。果然,那狸花猫看到老鼠,眼睛瞪得又大又圆。身上的毛倒竖起来,不待主人吩咐,喵的一声,便纵身一跃,扑了上去。这狸花猫实在是厉害,一口气便咬翻了数十只老鼠!那些个猫儿,见了老鼠,也都来了精神,一只接一只相继扑了上去,到处追咬。正在恶斗中的黑狗红了眼,它对身上的伤口已经麻木了。负了伤的黑狗没眨一下眼睛,就发动了新的进攻,必要置鼠群于死地。看准时机,黑狗发出一声声炸雷般的猛吼,化作黑色的旋风,朝前猛扑,又是一通死命撕咬。那鼠群虽说成千上万,但见了天敌,先自慌了。二叔和后生们,又先后点起了数十枝“火把”。鼠群再也扛不住了,四散奔逃,转眼间便逃得干干净净。
村民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过神来,看着满地血肉模糊的灰毛老鼠尸体,当真令人阵阵作呕,有些人更是张嘴吐了起来。二叔转脸,向那口肥猪的所在看去,不觉一怔,那头肥猪竟然不见了!二叔心里一慌,急忙奔到近前。方才只顾着和鼠群大战,地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大洞,黑洞洞的也不知深浅,那猪定是被拖入了洞穴深处。
二叔正犯着寻思,忽听得有人高喊道:“七爷,七爷怎么不见了?”那七爷便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一直藏身于西北角的老树上。好端端的,怎会不见了踪影?二叔找了一支手电,向下细细照去。赫然发现一只“长烟管”,正是七爷的心爱之物。想来,七爷定是看到肥猪被拖入了洞穴,他艺高人胆大,竟然也钻了进去。这时,有一些村民,也看出了情势不对,围了过来。
二叔把自己的推断,对众人简单的说了一下。便要带着黑狗下到洞穴,去接应七爷。众人哪肯让二叔一个人去犯险?当下选出来五、六个后生,人手一枝“五响翻子”,要陪着二叔一起探洞穴。
二叔打了个手势,黑狗便钻进了洞穴。二叔和那些后生,各自打着手电,紧紧地跟在黑狗的后面。那洞穴深处,却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虽然人人都拿着手电,也只不过能照亮前方两米的距离,再远的地方,那便是无尽的黑暗。
人在黑暗中行走,因为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心里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为防止发生意外,二叔特地又交代了一番。几个人在洞里走了几分钟后,大家的“方向感”就全没了。二叔倒不是太在意,只要有大黑狗在,这些都不算事儿。
走在队伍最后的,是一个叫大春的。他性子最是鲁莽,二叔怕他添乱,所以有意把他压在了队尾。说起来,大春是喝凉水塞牙缝,倒霉透了。在上个转弯处,他不小心崴脚了。按理来说,他应该立刻呼叫前面的队伍,但他为人过于好胜要强,暗暗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拖着右腿努力跟上。
又走了一段,大春的右腿脚踝处疼的越发厉害了。他用手电一照,自己也吓了一跳,那里肿的像是个馒头。他知道没法再跟下去,便对着前面大声喊着我二叔的名字:“虎子,虎子”。
二叔听见了,立刻摆手示意队伍停止前进,原地不动。大黑狗挺直了四腿,尾巴轻轻的晃了一下,在黑暗中的那双狗眼,闪闪发光。二叔拍了拍巨大的狗头,一个人向后找了过来。等两个人碰了面,二叔弄清了原委,又看了看大春的脚踝,耽搁不得。二叔当即决定,叫来一个后生,扶着大春原路返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后生搀扶着大春,打着手电慢慢的顺着来路往回走。才走了两个转弯口,大春就发现了问题,这路不对。周围实在是太黑了,两支手电筒照向远处,还是瞧得不太明白。大春黑着脸告诉后生:“我们方向走错了,这条路,我们压根没走过。”
后生是一脸懵逼。大春心里也觉得纳闷。这人下了洞穴,才走了多远?况且一路上,也没有看到有岔道啊。两人正犯着寻思,忽听得前方黑暗里,隐约传来几声狗吠。虽然听得不是很清,但大春和后生还是听出来了,是那只大黑狗发出的。
两人不禁呆了一呆。这是闹哪一出啊?怎么又绕到虎子那些人的前面来了?大春和后生想了想,还是打着手电,向着声音的方向摸了过去。
又走了好一段路,那狗吠声仍然是忽远忽近,飘忽不定,似是在引领着大春和后生。大春心里有些起疑,便站定了,不肯再往前去。后生的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安,在旁边悄声的说道:“大春哥,走了老半天了,那狗倒底在哪呢?要不,咱们喊两声试试?”
过了一会,大春轻声说道:“把手电都灭了”。后生微微一怔,随即照做了。四周顿时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大春又拉了拉后生的手,两人慢慢伏下身子。后生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这心跳得好厉害,和打鼓一般。
前面的黑暗处,又隐约传来了一些动静,但这次不是狗吠。大春慢慢用胳膊撞了撞身旁的后生,那人会意,两枝“五响翻子”同时顺过了枪管。又过了分把钟,只听得前面动静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仔细分辩,似乎是什么东西喘息的声音,好生的怪异。大春猛地打亮了手电,向前方照了过去。这手电的光亮并不好,但因为离的太近,大春和后生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大春那晚死在了当场,后生却侥幸活了下来,只是变成了疯子。后生一直到死,大伙儿在他嘴里,唯一听得明白的一句话是:“真的有鬼。”
走在最前面的大黑狗,忽然停了下来。摇晃着硕大的狗头,竖起了耳朵。不安的撮了撮鼻子,嗅着周围的空气,发出一阵粗闷的鼻息。二叔心里一紧,摸了摸那狗头。黑狗伸出舌头舔了舔二叔的手,不声不响地晃动着尾巴。二叔做了一个手势,大黑狗眦出了白森森的牙刀,伏低身子,慢慢地向前摸去。
转过弯来,大黑狗就在不远处,静静的卧着,无声的耸动着脸毛。二叔和三个伙伴,也随后赶了过来。几支手电照在了地上,大伙儿直瞧得脸色苍白,谁也作声不得。
地上扔着一把猎枪,那是县里有名儿的老猎人——七爷的心爱之物,枪身上却沾满了鲜血。二叔慢慢弯下腰,伸手去拾,那血,还没有全干!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句俗语:“枪在人在”的隐意。七爷如果还活着,断不会丢下这把猎枪。
二叔转脸问那几个同伴:“现在是回去,还是继续搜寻七爷?”一个后生鼓足了勇气,对二叔说:“虎子哥,七爷是县上有名的老猎人,他老人家都折在了这里,咱们还是先撤回去吧。”二叔知道这几个人是怕了,二叔自己心里也是有些发毛。
大黑狗却站了起来,暴躁地朝前跑了两步,又转回身来。前肢搭在二叔的身上,舔着二叔的手,轻轻的吠叫着。二叔想了想,还是跟着大黑狗向前走去。几个同伴略略迟疑,也都跟了上来。
约摸走了能有十来分钟,大黑狗再一次掉转过身来,绕着二叔兜起了圈子。洞穴里不通风,二叔等人提鼻子一闻,都不禁皱了皱眉头。前面传来的,是一股异味,熏得人一阵阵的作呕。几个人互相看了看,二叔冲他们摆了摆手,他一个人秉住这口气,悄悄的摸了过去。
手电照去,那是血肉模糊的一堆,有骨有肉。几个后生大着胆子摸了上来,看了一会儿,有人忍不住问道:“虎子哥,这会不会是?” 二叔“哼”了一声:“就是那头猪,这是被吃剩的。”话音未落,有人失声道:“那玩意儿,难道就在这附近?”
大黑狗突然纵身跳起,抖动着耳朵,发出阵阵低沉的吠叫。狗眼里冒出来兽性的凶狠,四条腿直直地挺立着,急促的摇摇尾巴,眦出如同刀锋一样锐利的牙齿。那牙齿,白生生的,在黑暗中看得格外的瘆人。二叔吸了口冷气,变了脸色:“那玩意儿就在这,咱们现在,怕是走不得了。”
大黑狗焦急地狂吠,蹬直了粗壮的后腿,随时准备扑过去。二叔将心一横,打了一声口哨。大黑狗一窜老远,直没入了黑暗里。二叔回过头看定几个同伴,脸上的表情有几分狰狞:“要走,你们只管走。我今天,要拼个鱼死网破”。
二叔一个人往前走去。他不用回头也知道,背后没有人跟上。他苦笑了一下,心头并不恨怨,反倒轻松了。生死有命,在此一搏。忽地,前面传来大黑狗,疯狂的吼叫声。大黑狗凶悍的战斗力,二叔是深知的。前年春天,村里闹开了狼,把村里的羊,先后拖走了四、五只。大黑狗被激怒了,不声不响地一路追踪,和狼群碰了个正着。最终大黑狗以一抵七,狗肚子被咬开,肠子都拖出来了,还是硬生生地咬死了七头饿狼。但现在面对的,是那个未知生物,大黑狗又有多少胜算呢?
据说人如果豁出去了一切,就不会畏惧死亡了。二叔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五响翻子”,直接冲了上去。



盘点全球奇闻异事 刷新你的三观
NO.1美国纽约,56岁妇女特里萨把无毛老鼠当宠物养,家中养有52只这样的老鼠,并和它们同枕而眠。她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坦言,别人称呼她为鼠女士,这个嗜好很多人不能接受而拒绝与她交往,她感到困惑。NO.2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61岁的巴西男子泽立·罗西(ZeliRossi)与妻子一起展示他是怎么睡在棺材中的。据报道,罗西为了纪念他死去的朋友,坚持在每周五晚上到棺材中过夜,这一习惯从未间断,已持续了23年。
NO.3俄罗斯彼得罗扎沃茨克,两年前发现的被认为是外星人的不明物体,被保存在冰箱中长达两年之久。2009年,一名当地女孩在一个不明飞行物坠毁处发现了这具尸,于是她就用塑料膜将其包好放入冰箱中。目前,它是不是外星物体还不得而知,但照片公布后立即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NO.4莫斯科一洗车店推出了性感比基尼美女洗车服务。
NO.5印度拉贾斯坦邦比卡内尔附近的Kilchu村,当地妇女ChouthiBai以母乳喂养一头牛犊。她每天都要给这头牛犊喂3-4次奶。她觉得这是很自然,很神圣的一件事。她说这只小牛的妈妈已经死了,自己的孩子也已经3岁了,用不着喝那么多母乳。现在她的母乳能养大这只小牛是一件好事。而且这只小牛很乖,喜欢趴在她腿上。除了她的乳汁,她还会喂小牛印度的传统面包。
NO.6单身母亲娜达雅·苏里曼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名女人,现在甚至有个新词汇专门用在她身上:octo-mom(八胞胎的母亲)。她在2009年2月生下了八胞胎。在此之前,她已经有六个小孩(包括一对双胞胎),都是靠人工受孕生下的,小孩的父亲是同一个人。
NO.7据英国《世界新闻报》报道,英国一名女孩埃利奥特·史密斯在一岁时就被诊断患上早年衰老综合症(早衰症)。小女孩今年8岁,看上去却像是一名老人了,且皮肤看上去呈淡绿色。医生称,她的衰老速度比常人快8倍,这意味着当她10岁时,实际外貌是80岁的老太太了。
NO.8生活在美国迈阿密的DominiqueLanoise今年40岁,是6个孩子的母亲。因为体重暴涨到超过45英石(约合286公斤),她已有16年足不出户。由于胖到找不到尺寸适合的衣服穿,她只能整天赤身的坐在床上,由孩子们照顾她的饮食。得益于为胃部手术准备的流质食谱,她的体重最近终于开始有所减轻。这位单亲妈妈说:“我曾经非常瘦,但自从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我就变胖了。”她在16岁那年生下第一个女儿,女儿现在已经24岁。
NO.9居住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Spartanburg的24岁小伙儿道戈·弗比斯由于患有先天骶骨发育不全症而在婴儿时期就进行了截肢。但是凭借坚强的毅力,他现在成为了一名老师。此外,他还有一个女朋友。
NO.10来自美国的8岁的AimeeMilota和7岁的GraycenBeardslee双双深受着色性干皮病(XP,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对阳光严重过敏)的困扰。因此,这两个小女孩不得不始终在黑暗中生活,否则皮肤一旦在日光下暴晒几秒就会得上皮肤癌,进而慢慢死去。为此,她们自家的房子也都是防紫外线的,身上穿的也都是特制的防护服。两个小女孩也因疾病而结缘,成了很好的朋友。

世界奇闻异事大全,你听过哪些?
世界之大,充斥着各种奇闻趣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奇闻趣事吧。
“见钱眼开”的古井——曾出土“马踏飞燕”的武威雷台汉墓里的一口汉代古井长期以来吸引着游客的眼球,此井居然“见钱眼开”:能将扔进井里的钱币神奇地放大。据考证,这口古井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渐干涸。有人做了试验,用同样的参照物,在别的井里却没有放大的现象。
汕头市达濠区渔政局从渔民获悉一条震惊达濠的消息,一只体型庞大,性情极其凶猛的大水怪出现在人们眼前,这只大水怪听说要十位壮汉才挪动它 。
蝾螈是最广为人知的墨西哥火蜥蜴。这一物种最初在墨西哥城下的湖泊中发现。蝾螈在科学研究领域大有用,在生长到18-24个月的时候,蝾螈进入性成熟期。而蝾螈雄雌间的交配行为亦相当特殊的,雄性个体会将其精液包在一个如胶囊般的精荚中,当排出体外时便会在短短的时间内由雌体吸入体中,以完成交配行为;
左、右手之谜——作为万物之灵的有着灵巧双手的人类,左手与右手的使用概率却极不相同。大多数的人习惯于用右手,而使用左手的人仅占世界人口的6%~12%,为何比例如此悬殊?有的人试图从左、右脑的不同功能,即做与想的密切关系以及心脏的位置等角度来解释人们为什么大多数都习惯用右手这一问题,然而,并未获得圆满的答案。


 朗读本文
朗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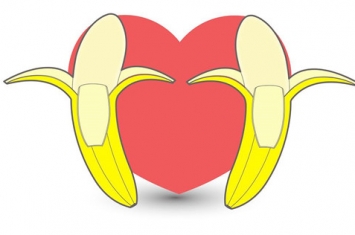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