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一个十分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一批特殊的人。这些大师在课堂上,流传着许多的“奇闻趣事”。
黄侃:我是名士,所以狷狂
黄侃是从章太炎,被称为“国学大师”,是“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的学生,如杨伯峻、程千帆、潘重规、陆宗达、殷孟伦、刘赜、黄焯等,每一个人拿出来,都是可以称为“大师”的。而他在课堂上,也是别具一格。

黄侃在北大教书时,每讲到关键时刻,便卖个关子:“这个地方有个秘密,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还不足以让我讲,你们要听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有一次,到了上课时间,教室里已经坐满了学生,可黄侃迟迟未到。学生等了好一会儿,见老师还未来,便去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的人知道他名士的脾气又来了,便小心翼翼地找到了他,低下身子说:“先生,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不料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上课时间是到了,可是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还未及时发放工资。于是教务处急忙跑去帮他领来工资,他这才去上课。
黄侃最最喜欢的事情可能就是开胡适的玩笑了吧。胡适提倡白话文,而他则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一次上课,谈论到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时,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对于黄侃的为人,很多人是不满意,因为他好色,狂狷,孤傲,好骂人,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性情乖张,特立独行……周作人曾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但无论如何,对于这么一位名士,他留给人们的,除了这些“奇闻趣事”之外,更有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一个人有多大的本事,就有多大的脾气,放在他身上,正是再合适不过了。比较可惜的是,他说五十之前不著书,可是还未到五十,他就离开了人世。
刘文典:民国风骨,狂傲不羁
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
他一生最佩服的是陈寅恪。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有一次,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五个字就行了。众学生听得一头雾水,甚是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他讲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下午的课,要讲到五点多,才勉强结束。他讲课时喜欢旁征博引,讲授《文选》时,往往一节课只讲一句,还上不完。一个学期过去了,《海赋》还只讲了一半。每每讲到得意时,就会高声吟诵,还要求学生跟着吟诵。对于不吟诵的学生,他并不责骂,只是说:“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他讲课时,吴宓总爱来听,坐在最后一排。他喜欢闭目讲课,讲到自己觉得独到之处,忽然抬起头,对最后一排的吴宓说:“雨僧兄以为如何?”这时,吴宓便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下面的学生窃笑。
刘文典虽然狂傲,治学却十分严谨。“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他的治学格言。他没有虚伪,没有假道学,一生诙谐,善谈笑。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他却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陈寅恪: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高山仰止,令人叹服。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时,是当时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常被成为“教授的教授”、“活字典”。他讲课时,吴宓是风雨无阻,每堂必到。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
陈寅恪讲课的内容很广,宗教、历史、语言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上课时曾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1932年,清华大学在新生考试时,刘文典邀请陈寅恪出题目。陈寅恪匆匆出了一篇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另外还有一副对子:“孙行者”。
看到这副对子,已经很久不作对子的莘莘学子一时懵了,一半以上都交了白卷。当时仅有一人对了“祖冲之”而得了满分,这人就是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当时很多人对清华大学还出对对子的题目,觉得清华食古不化,提出了批评。但陈寅恪却给出了四条理由:
一、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
二、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
三、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四、考察考生思想条理。
陈寅恪治学之广之深,不得不令人叹服,否则也不会说出“四不教”的话来。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学问家的广博,一个哲人的深邃,一个教师的责任。
乱世出英雄,民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三位大师“特立独行”,让我们见识到了为什么那个时代能出现那么多的“大师”。反观当今社会,我们确实缺少一些这样学问深厚、特立独行的老师。


 朗读本文
朗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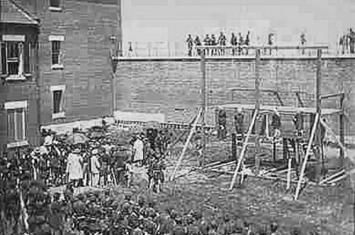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