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出租屋拿到钥匙,我飞快的往目的地赶了过去,一路上一直跟小王保持着联系,我过去毕竟需要一些时间,如果周佳星在我到达之前完事走人了,就没法将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逮个正着,给小王打电话,就是让他替我看着点。
二十多分钟过后,我来到了小区。小王这时就守在楼下,看到我后立即凑了过来,告诉我美娜带回家的男人还没有出来。
带着愤怒,带上小王,我直接奔上了楼,还未靠近屋门,就听到了响亮的电视机声,刻意把声音开这么大,十有八九是在掩饰她俩正在干的羞耻之事!
借助电视机响声的掩护,我小心翼翼的掏出了钥匙,随后慢慢的插入了钥匙孔,再轻轻一扭,“咔呲”一声,房门就顺利的被打开了。
我刚进门,就看到了美娜跟周佳星!美娜一脸恐慌,周佳星则一脸无措,两人虽然面对面坐在沙发上,衣衫整齐,没有正在做着见不得的事,但他们的反应已经将自己出卖!
“林美娜!你竟然敢把男人带回家!你个不要脸的荡妇!”
既然她如此无视我的警告,我自然不会再给她留情面,大骂一声就冲了过去,打算狠狠的甩她一个耳光,发泄自己的不满。不想周佳星这时竟冲了上来,还猛的推了我一把,他比我强壮,力道很大,把我给硬生生推倒在了地上!
“去你妈的你竟然还敢动手!”
我大骂着迅速爬了起来,周佳星也在这时大喊了一声:“李晋老弟你误会我了!”
“我误会你马勒戈壁!”
辱骂过后,我直接冲向了周佳星,抡起拳头就是一记重锤,不料他稍稍一躲,就把我给晃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他紧接着就抓住了我的手,然后一掰,猛的一发力,反将我给制服了!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我死死给控制住了,这混蛋显然是个练家子!
明知干不过他,我只能朝愣在门口的小王喊道:“你傻愣着干什么?还不去叫人!”
我这一喊,小王立马就惊醒了过来,拔腿就往楼道跑了出去。见小王要跑,周佳星随手将我扔到了一边,飞身追了上去,也就几秒钟时间,我就听到了一声大喊,没多久,小王就让周佳星给拎了回来!
“李晋老弟,你真的误会我了!我跟美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我今天过来看我一个远房亲戚,正好在楼下碰到了她,才知道她住在这里,既然碰了面,我们就聊上了,美娜只是请我到家里坐一会儿,我们是清白的。”
鬼才会相信周佳星的解释,但他是练家子,又干不过他,跟他来硬的估计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老公,你真的误会我跟周总了!周总说的是事实,我们确实是偶然碰到的,他说想到家里来看看,我不好意思拒绝,就把他给带了进来,我们真的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
周佳星才解释完,美娜就十分配合的附和道,我不相信他们的解释,不满的对美娜责问道:“你明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为何还要将他带进屋?”
“我……”
美娜犹豫了,迟疑了,在我看来,她这是心虚了!
“这不怪美娜,是我非要进来看看的,我要是知道你是个疑心这么重的男人,就绝对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看到美娜哑口无言,周佳星立即将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还说起我来了!不得不说他俩的戏演的是真好!
“我昨天晚上就看到你鬼鬼祟祟的出现在小区里,发现我盯上你之后还想方设法的摆脱我,为了躲避我,你都他妈躲到花丛里了!你还好意思说是来看什么突然冒出来的远房亲戚?你们撒谎能不能撒的认真一点?能不能想个更实际一点的借口?”

村里人以为我是瞎子的小说叫啥名
《盲欲》。该小说是由网络作家月下销魂创作的一部网络都市小说,讲述了男主因眼盲在城市中闯荡,后因一次意外,眼睛恢复并获得寻常能力的故事,但是村里的人还以为男主是瞎子,该小说于2021年上市,一经上市便受到广大读者青睐,截至2022年该小说处于连载中,在QQ阅读便可观看。
我渡过山,渡过水,却不知道,该如何渡自己出凡尘
回忆就像是在给自己自己做解刨,从外部的皮毛开始,一层一层地剖开,只为寻回命中关于生了根的苦海情深。终于有勇气在这里说出自己的几十年经历,还都只挑重点来说,两万字的十几年人生,就让我浪费了800抽的纸巾。
是我太过认真,把一切过往放在心底等来生。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正视和勇敢地接受我自己的过往,虽然码字的时候泪眼汪汪,感性占据主导地位,但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开端,抑或是一个结尾。
突然好想给自己写一本传记,再配上几首词,用来渡我过去的灵魂,等它在来生获得重生。
我用几十年来渡自己的爱和恨,却渡不过自己的苦海和命运的离分。
我在小学的时候以为上了初中就好了,能远离母亲;上初中的时候以为上高中就好了,上高中的时候以为上大学就好了……
谁知,这是一个死循环。
一定是我前世用尽了缘分,这一生才没有亲情和家庭的情深。
而关于那些记忆,真的是一步一生根。
精神折磨远远大于肉体折磨,我也没有形成什么系统性有逻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如何逃离上,就像一个叛逃的将士被人追杀,时刻都在想象自己该往哪儿逃,才能保下小命。
我原以为,抛弃是最大的不可原谅,其实,精神折磨才是人生第一大苦楚。
我不知道,父母是否会觉得自己的教育方式有何不妥,他们是否会在深夜自我反思?可多少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躺在小木床上,泪眼唰唰地打湿着枕巾,一遍又一遍。
我没有同龄孩子的活泼与可爱。就像一个被揠苗助长的小大人,沉稳得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难以忘记冬夜漫长的夜幕茫茫,有位孩子矗立在雪堆旁,看着山峰的模样。
原本母亲是不同意我上大学的,还好,通知书是到学校去拿的,不然,我难以想象,我接下来的人生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虽然现在也不尽人意,但起码,流浪也好过就地彷徨。
我的离开是那么的落寞,又那么孤寂,又那么决绝。
一个人的离开,带着永别的心态,不再回来。
我没有坚强的内心,也没有强大的意志力,我只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普通的凡人,只要不在这个伤心的小山村,只要不在有他们的地方,我以为,我就能就此流浪远方。
可事实是我错了,没有人能逃离,包括我,至今也未能逃离划在心底的牢笼。
提着我那少得可怜的行李,头也没有回,本想着,在车站的时候给父亲一个离别的拥抱,但是他在半路就把我扔下了,所以,这个拥抱到现在也没有送出去。
我生着那样的怪病,也不知自己会在何时何地殒命与他乡,但只要不是家乡,一切便好。
很多时候,我不像是个人间的人,更像是个来渡劫的小仙,定要历经多少劫难才能修成正道似的。
外面的世界很大,也很浮躁。唯我,心如止水。没有社交,没有朋友,焊死的牢门再也不想打开。
大学生活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丰富多彩,活动也几乎不参加,与同学的交流也甚少,就是三点一线的生活,只是空余时间多了起来,我有了挣钱的机会。
第一学期,与母亲没有任何联系,是我这些年以来过得最充实的时光。即使还是不会笑,但起码,我觉得我涅槃了。
也尽量不去怀念那些辛酸的过往,多想,时间就停留在那点,不再改变,我便于此苟活几年。
按理说,我应该有一颗坚如磐石的心才对,可偏偏,就落下来这心软的毛病。
我想,我是继承了父亲的优柔寡断吧。呵,遗传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一言难尽,由不得任何人。
这里,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父母也不再与老师相熟,也没有其他相熟的人,我就像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独自生活在这里。
上完课,大家就各自散了,除了睡觉,其他时间我几乎不在寝室,自然,与室友的关系也是淡如水的地步。
不知何时,我竟也这么淡薄了。
若非为人,我真想做天空翱翔的鸟儿,天高任我飞,山川大地任我游。
就在我以为我踏上了生活的列车时,不幸却总是让我应接不暇,这简直比小说还狗血的情节就这样硬生生地降临在了我身上。
在喝了两瓶北京二锅头的我并未醉,听了些伤心的歌曲,在凌晨2点昏昏睡去。
第二天醒来的我,嘶哑的嗓子在发出几个声响之后就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我想着是昨夜的酒太烈了,多喝点水休息休息就会好的。
奈何,事与愿违,不要把不确定的事情想得太好, 往往,事情都会朝着糟糕的方向发展。
就这样过了两天,我尝试着用喉咙发出声音,但并未见效,而且喉咙感觉有丝丝的痛感。
我意识到,我应该去医院。
做了一些列检查,医生只发现喉咙红肿,声带并未受损,医生也很意外,也许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时,我多想自己是个演员多好,给医生来个反转。
我没有丝毫地慌张,不能言语又如何呢。日后便少了许多口舌之争。
于是,医生开了一些消炎的药给我,我就回到了宿舍,恰好父亲打来电话,我挂断了电话他又继续打,反复了很多次。
给他回了短信,说我喉咙发炎说话不方便。
可是父亲还是打来了电话,我接了也无法说话。他在那头生气地指责我为何要去医院浪费钱,说我一点儿也不珍惜他的劳动果实。
不知他是否忘记,两月没有给我生活费的是是否饿死或者饿晕在某个角落里呢?
现在要饿死一个成年人还是很难的。更何况我还一直做着兼职,养活自己完全没有问题,也不开口问他要生活费,一切随意,他愿意给我也不拒绝。
我在心底冷笑,母亲的感染力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就连父亲现在说话的语气也与母亲如出一辙。
首先是劈头盖脸地谩骂,接着是指责,然后是发泄心中的怨气。
他的原意是说因为他放任了我去上大学,导致他在家里要遭受母亲的责骂与埋怨,这一切的因果都出在我身上。
虽然我也很抱歉,但是我并无解决的办法。
在很多年前,也就是我还小学的时候,唯一的解决办法,被他否决了,之后,我便再也不会提及。
毕竟,在他们眼里,我连一个外人都不如。至少,他们还会投以微笑给外人,可对于我,却从不会,这就是陌生人与家人的区别吧。
人总是把自己的好的秉性呈现给别人,却把不好的甚至怨气发泄到身边人的身上。既然内心不满,又何必伪装成一个好人?
不知是几世修炼来的福分,我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到了大学的人生。
父亲发泄完了,我没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骂骂咧咧中挂了电话。
我知道,他还未解气。过几天他还会卷土重来。而我,只需要静静地听着就行。
抑郁症就像是身体里的血液,时刻在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流淌,所到之处,都留下它独特的痕迹。
我站在江面上的大桥上,看着天边的半弦月,在低头看看脚下湍急的江水,也不知,这一汪江水能否带我远离这闹市的喧嚣和这一世的悲哀。
我这一生,不求轮回,也不想渡自己远离苦海情深,只愿,了结此生,来生不喜。
桥上站着另一个白衣女孩,斜眼望去,眼角还有未干的泪痕,估计不是苦海就是情深。
荒烟孤城,没有值得等待的人,渡过几十年的夜晚和天明,渡不过今晚的月明。
良久,她叹了口气,跳了下去,像是在为自己的一生划一个感叹号。
我并未去拉她,也没有叫住她,我是死过一次的人,对生死看得很淡,薄如鸿毛。
一个人的离开,不管是经过深思熟虑还是一时冲动,都是自己的选择,我又有很资格去干涉别人的人生呢?
也许会有人说我冷漠,没有人情味。
可人情味又能干嘛呢?我不需要。也不知道人情味是否能拯救一个濒临死亡边缘的灵魂?
周边的人报了警,来了警察,消防队,救护车,我在桥上目睹着这一切,像是个来收取灵魂的摆渡人,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女孩被救了起来,没有一丝喜悦,她躺在担架上的侧脸写着生无可恋几个字,我知道,这不是她的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咽了咽口水,缓慢地离开,我终究还是没有勇气在那一刻离开,似乎有什么挂念,可是根本没有。
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这样的情况。
在我没有回家的第一个寒假,一个研三的师姐从楼上自由落体运动,落在刚好路过的我面前,我就这样静静地在那里站了一分钟,不是惊慌和害怕,只是在想,她下来时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和有多绝望吧。
我也曾在10楼的走廊眺望远方,看划过天空的星辰,最后,还是选择了留下。
我依然不能说话,期间,父亲又打来电话发泄内心的怨气,我就像是个垃圾桶,要承载他在家里所受的委屈和不忿。
没有关爱,没有问候,连言语都带着冰冷的气息。
而我,早已习以为常,这些,在我的寒潭甚至都激不起涟漪。
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狂风暴雨,是我最喜欢的天气,只有在这样的天气,人才能无法安静下思绪来回忆。
也许,考验周期到了,我突然又能开口说话了,就像上天想收回赐予你的某种功能,在考验结束后又返还给你一样,期间的过程有点像过山车,斗转星移,最后,除了记忆深刻,其他并未失去分毫。
我从不主动与父亲联系,因为我知道,我的主动换来的会是更多的倾倒,我不主动,也是在给自己规避一些不必要的 情感 磨难。
就在我以为我终于摆脱狂躁的母亲时,母亲又开始对我电话轰炸了,虽然一年多未见了,她的脾气却见长,说话更难听了,一边在电话里骂父亲,一边骂我。
很多时候我都会在听她骂我半天之后回她一句:你骂完了吗?骂完了我就挂电话了。
很明显,她总是被我这句话逗得更加生气,然后会加倍地骂我,很多时候,我都这样故意激怒她。
这是我对她的报复,哪怕她可以连续几天打电话来骂我,我依然在她骂了半天后冒出这句话,每次听到她在电话那端暴跳如雷,我心里就会油然而生些许快感。
大学四年,我总共回去了两次,不是说好了逃离的地方,却不知道心里是如何想的,还是在中途回去了。
周围的环境变化并不大,只是父母的变化比较大,父亲不再开客运车,公交车挤掉了他们客运车辆的最后一点生存线路。
母亲不再像以前那样年轻,鬓角也开始有了少许的白发,我不在的这几年,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或许是岁月的洗礼吧。
但性格却有增无少,更加地惹人恨。
看到她的青丝秀发在岁月中变色,我心中感叹,她也有老的一天,除了不屑,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
反常的是,我两次回去的第一天,她都对我出奇地好,好像这就是她的本来面目似的,对我驱寒问暖,问我想吃什么,喜欢吃什么,我都冷冷地回她:随便,没有喜欢吃的。
又何必在我面前装腔作势,扮演慈母的角色呢?
我可不是当初那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黄毛丫头了,用她的话说就是我翅膀硬了,就不把她放在眼里了,其实只是我的心坚硬了而已。
每每,她至多也只能装上一天,第二天就原形毕露,一早就开始对我骂骂咧咧,似乎除了骂我,她再也找不到其他乐趣似的,而我,只能无视她,也不理会她,独自干着自己的事情。
越是这样,她越气愤,有时候甚至把我做的饭菜一股脑倒进潲水桶,她不吃,大家都别吃。我也不会再去做第二次,只有父亲,会默默地去重做。
我不在的这些年,估计他就是这样过来的吧。但是我觉得他活该,自己的纵容换来的结果,除了自己承受还能如何呢?
索性,为了多换些清净的日子,我在离开的时候都会选择与她大吵一架之后离开,我知道这样,她许久都不会再来骚扰我,我也可以获得短暂的宁静。
有时,烦了,也会把她电话拉进黑名单,久了,她就会找别人的电话给我打,如此反复,我又把她从黑名单里除去。
也不知道,她与哥哥打电话是如何的,我只知道,我在的时候,她与哥哥说话的细声软语,简直与对我是天壤之别。
仿佛是身体里住着两个灵魂,面对不同的人也是不同的灵魂。
后来,机缘巧合,认识了心理学院的一个同学,他给我推荐了他的老师,我第一次去看了心理,也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伤口撕裂看展现在别人的面前。
也很感谢这位老师,对我免费的心理疏导,让我在那些活不下去的日日夜夜,抓住了些许的生的欲望。
母亲总是那么地刚强,什么都想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只要不遂她的意,迎接的便是诅咒和辱骂,我不知道,性格温和的外婆和秉性良好的外公为何会教导出如此骄纵的女儿。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外孙女是在怎样的煎熬下成长。
在无数个想要撇下这个世界的念头里,熬了四年,心性也并未变得成熟,更多的是忧愁善感。深深地陷在自己的泥潭里,无法自拔。
既然选择了流浪,就浪迹天涯吧。放弃了读研的机会,选择了烦躁的 社会 ,母亲再次对我下命令,要求我回老家去考公务员,因为在她的认知里,除了公务员、医生、教师等职业,其他的都不是正当职业。
可我偏要和她反着来,与她对着干,她在意的,我偏偏要反着来。
所以,我果断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她见不能像以前那样控制我,便发动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来对我轮番劝阻,我又岂会轻易妥协?
我苦难时未见一人伸出援手,我毕业了,一群人就开始在我面前演绎亲情可贵的戏码了?
我如今早已不吃那一套了。
好不容易,跳出了沼泽,又岂有再往里跳的缘由?
见我无法掌控,藏在他们心底的真实想法就像橄榄枝一样,伸出来,摆在我眼前,只要我不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做,就让我还这些年花在我身上的钱,对,没有看错,也就是抚养费。
当时,我听这话从父亲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是有点震惊的,为何?这是何道理?
我当时听了气不过,就答应了他,说会按月来还,每月工资的一般还给他们,当然也没有说具体是多少数目,我很久未与他们生过气,但这一次我真的有点气不过,所以直接就答应了,甚至都没有问具体的数额是多少。
我每天拼命地工作,就想早日断绝这层关系,从此,孤身天涯也好过每日被折磨得强。
至此,他们也很少打电话来骂我,更多的是我钱打晚了,打电话来催促而已。
持续了一年,我就不再打了,心想,凭什么,凭什么你叫我干嘛我就干嘛,你叫我归还抚养费我就乖乖地归还?大不了,大家法庭见好了。
结果是,二老轮番打来电话辱骂我,说我去当小姐,说我去卖,说我嫁不出去,说我到处勾搭老男人……
这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些话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说得出口的。
但是他们的诅咒很厉害,我至今没有嫁出去,因为我害怕成为母亲那样凶神恶煞的人,也害怕找到一个父亲那样优柔寡断的人。
我也害怕我找到人嫁得出去,迁户口的时候像我同学一样,被要巨额抚养费。
而他们现在手里唯一的筹码就是我的户口。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好像好运从来不会降临我身上一样,我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却还要往上升级磨难的等级。
我突然耳聋了,犹如晴天霹雳。我只好辞职去医院治疗,一个人去医院的滋味真的不好受,每个夜晚,护士来查房问我的陪护的时候我都说我是一个人,但是每天醒来,床头都有打好的开水,也不知道是谁打的,但是心里还是很感激的。当然,也有催费单。
医生没有查到是何原因,什么检查都做了,但是依然找不到原因,就像那次突然失声一样,但是耳聋不一样,耳聋让我听不到任何的言语,所以我才会选择入院治疗。
期间,父亲打来电话,我无法接听,只能发短信说我耳聋了在医院,结果,他就发短信骂我,说我有钱给医院都没钱给他们。
我……我当时真的很想给自己两耳光,为何自己要自讨没趣呢?干嘛要告诉一个从来不会关心你的人你生病了呢?
我冰凉的心再一次地,冻到不能再冻。
看着病房里其他病友的家属,关爱,陪伴。眼泪又不争气地装满了眼眶,牙齿被咬得滋滋响,真的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命运啊!
眼泪总是很会来事,总是把你的思绪拉到你并不愿去的场景,只为了它自己更加的畅快淋漓。
后来,耳聋终于治好百分之七十了,也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我休整了一年,整日躲在出租屋里,害怕出去见人,也害怕阳光,我害怕,害怕阳光一照,我的心就要被晒穿一样。
我都昼伏夜出,直到天完全黑了,我才挪动脚步去菜市场买点小菜,顺便在夜色中叹口气,询问自己的内心,为何还活着?
而关于我此前的人生,没有得到一分一厘的爱,却只留下十分的怨恨,是否是我太过认真?总在爱与恨之间较真?
我才发现,好久未犯的抑郁症,又悄无声息地在我这里重新生了根,每天都在屋里哭泣,苦累了就睡觉,有时候也会跑到楼顶,周围的灯红酒绿,却容不下我这小小的卑微的灵魂,我该拿什么渡过我的人生?
不知道其他人是如何渡过那些难熬的时光,我真的是度日如年,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与死神争夺时间。
时间多了,人就更容易胡思乱想,我想打破眼前的残局,于是便重新找了工作,即使不开心,不快乐。那又如何呢?也只是一只苟活于世的灵魂而已,又何必那么较真?
没有了刚出校门的激情,生活也没有了斗志,像行尸走肉般地往返单位和出租屋,但是却少了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
是我太没有又勇气,总是在心底生起子虚乌有的期待。
可是在这两年,抑郁症即使吃了药也不起什么作用了,每天都有轻生的念头,虽然与父母联系少了很多,但今生的记忆早已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间,又如何能关于从前的纷纷。
我又辞职了,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很好的用现在的状态去完成工作了,也不想给公司带去不必要的麻烦,虽然领导一直挽留,但是我去意已决,就像我当初要逃离一样。
每天关起门来,又开始了封闭的生活,左洛复吃了也不怎么管用,依然每一天都在死亡边缘徘徊,却还是下不了决心,为了让自己活下去,每天都在寻找让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像个传销大师一样,白天给自己洗脑,夜晚的时候又重回死亡边缘,如此往复,日复一日地活着,人不人,鬼不鬼。
这期间我回了一次老家,与母亲彻底闹翻了,从此拉黑了她的电话,她也再没有用其他人的电话打来,我想我与她的缘分应该就此了解了吧。
如果我还在,在她需要我赡养的时候,我依然会出我该出的赡养费,我会按照法律义务赡养她,但是却不想再与她相见了。
这两年,很清净,也很痛苦,清净的是母亲彻底没有联系我,痛苦的是整日寻找生的希望,就在我想重返职场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被 社会 所遗弃了,我脱离 社会 太久,再也不能融入其中了。
也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还能坚持多久,下一个天明是否会朝霞红光漫天,黄昏的晚霞是否会映红半边天空。
我在等,每天都在等,等自己活下去的每一个转身。
我渡过山,渡过水,却不知道,该如何渡自己出凡尘。


 朗读本文
朗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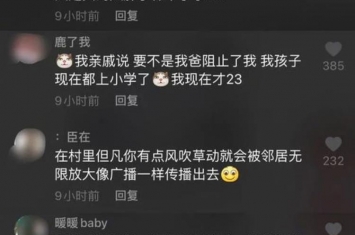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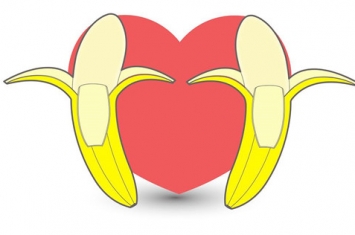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