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其“物竞天择”的说法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呼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进化论传入中国,其理论内容实际上是经过了两重扭曲的:第一重是,严复翻译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而不是达尔文本人的《物种起源》,因此并没有真正引介达尔文对于科学证据、实验、假说对比等等的讨论,也就是说,进化论传入中国时,是被当作一种社会理论,而不是自然科学理论来对待的。
第二重扭曲是,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其实不能算严格的翻译,而是塞入了自已的许多私货。很多人因为《天演论》对赫胥黎有误解,以为他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实则不然。赫胥黎和斯宾塞不同。斯宾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始作俑者,认为社会竞争和自然选择一样,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不仅是亘古不变的事实,也是应当用于指导人类行为的准则;而赫胥黎则反对把生物界与人类社会做简单地类比,认为除了自然本能以外,人还有价值观、伦理、责任感,正是这些道德情操与原则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因此他一方面心甘情愿做“达尔文门下走狗”,另一方面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决反对者。
《天演论》是严复对赫胥黎《进化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的译文,但又不仅仅是译文。严复在《天演论》里夹带私货,塞进了自己救亡图存的思想,恰恰反驳了赫胥黎那些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张。历史在这里玩了一个吊诡:一本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被译介进来,却成为了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经典文本,让后来不少中国人对进化论产生了严重的误解。
不过这也不能完全算作偶然,一方面救亡图存确是一时之亟,另一方面就世界(至少欧洲)范围而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学也风头正健,赫胥黎的伦理学正被越来越多人看作过了时的、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空谈呢。一直要等到两场世界大战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才会受到全面的反思。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植物的良种培优,蚕种的选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达尔文在进行进化论论述时,还引用过一些中国的农学书中的事例。清末西学东鉴,达尔文主义对唤醒国人认同,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些人根据家生野化现像,来猜测中国周边或偏远地区的猴类其实是中国古书中记载的某些族群。(简而言之一句话,再不努力像个人样,大家就……)


 朗读本文
朗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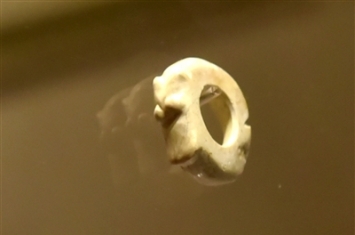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