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嘉诚丨文
近日,“蛙儿子”的旅行照和生活照成为了微信朋友圈中每天必出现的内容。这款名为“旅行青蛙”的养成类游戏以其特有的佛系风格,让许多青年男女们体验了一把“为人父母”的心情。作为一款日本游戏,蛙儿子们的旅行照让我们间接了解到许多日本的名胜古迹。假使有一天,旅行青蛙穿越到了宋代的中国,它们会经历怎样的体验,我们每天又会收到怎样的明信片呢?

吉凶叵测的江南之旅
既然穿越到宋代中国,那么帝都汴梁自然是不容错过。或许睡眼惺忪的蛙爸蛙妈们在清晨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蛙儿子畅游在汴河中,欣赏着两岸如《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那般繁荣、喧闹。作为一只青蛙,天清寺前的“虾蟆窝”和琼林苑中的“虾蟆亭”自然也是值得一去的旅游景点。顺便去瞧一瞧被开封士人戏称为“虾蟆”的书店老板陈嘉言也不错。
当旅行青蛙准备离开汴梁城,继续宋代之旅之时,想必开封的朋友们一定会善意地提醒它:“莫向南方去,将君煮作羹。”这个提醒并非空穴来风,如果青蛙南下前往临安城游玩,第二天我们收到的旅行照也许就是它们被杭州城的农夫们塞进冬瓜的场景。
在宋代,食蛙、吃河豚的江浙人士无疑是宋人眼中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群体。在《尔雅》中,蛙被称为“水鸭”,而在江浙一带,青蛙也被称作是“水鸡”、“坐鱼”。当时去江浙为官的外地官员,几乎毫无例外的都会对于本地人的食蛙习俗感到怪异和不解。当然吃货们显然是无视那些流言蜚语的,在北宋时期,一位在浙江为官的宗室子弟,因为沉迷于蛙肉无法自拔而受到了其他皇亲的嘲笑,为了堵上亲戚们的嘴,他将蛙腿做成肉干后送与他们食用,然后才道出这是蛙肉,之后舆论对于东南人食用蛙肉的嘲讽便马上减弱了。看来在美食面前,我们真是一脉相承地继承了宋人的基因。“闽、浙人食蛙,中州人每笑东南人食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两股脯之,给其族人为鹑腊,既食然后告之,由是东南谤少息。”(《萍洲可谈》卷二)
在南宋初年,鉴于高宗皇后个人对于食蛙的反感(一种说法是觉得其酷似人形),极力劝说高宗下诏禁止食用青蛙,但是区区禁令怎么可能阻止江浙人对于此等美味的追求,很快买卖青蛙的黑市便迅速出现。销售者通过挖空的冬瓜作为掩护,将大量青蛙塞入其中,运送到秘密集市进行贩卖,甚至出现了“送冬瓜”这种专门的蛙市黑话。一些食蛙爱好者也通过行话结下了深缘,黄公度在福建为官之时,令庖兵去买坐鱼三斤,庖兵不解其意,问遍诸生无人能晓,唯有州学录林执善告诉他去买三斤青蛙,据说林因此获得了黄公度的极力赏识。“杭人嗜田鸡如炙,即蛙也。宪圣渡南,以其酷似人形,力赞高宗申严禁止之。今都人习此味不能止,售者至刳冬瓜以实之,置诸食蛙者之门,谓之‘送冬瓜’。黄公度帅闽,以闽号为多进士,未必谙贯宿,戒庖兵市坐鱼三斤。庖兵不晓所名,遍问诸生,莫能喻。时林执善为州学录,或语庖人以执善多记,庖人拜而问焉。执善语以可供田鸡三斤,庖人如教纳入。黄公度笑而进庖人曰:‘谁教汝?’庖以执善告。黄公遂馆林于宾阁云。”(《四朝闻见录》)
可见,相比于开封城,旅行到临安的青蛙们似乎不太安全,稍有不慎便会有被塞进冬瓜的生命危险。但是作为南方第一大都市以及南宋的都城,让爱旅行的青蛙避开此地未免也有些遗憾。考虑到外形上的接近,它们或许可以向开封的蟾蜍朋友借一套外衣作为伪装。那么,如果是以蟾蜍的形象出现在临安,它们会遇到怎样的奇特经历呢?

日本浮世绘大师河鍋暁斎创作的蛙蛤合战
作为一只宋代的蟾蜍
虽然宋代人不可能像现代生物学一样对青蛙和蟾蜍作出精准分类,但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就知道,它们是两种看起来类似却完全不一样的生物,因而二者发展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含义。如果说青蛙是作为一种富有特色的地方食物,那么蟾蜍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就要复杂得多。自古以来,蟾蜍都被当作是一种长寿的生物,抱朴子云:“蟾蜍寿至千岁者,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字。”追求长生不老的道士们自然是不会放过这种可能让他们续命的生物。据说南朝的刘亮就用白色的蟾蜍作为材料炼丹以求延年,但最后不仅续命未成,反遭丹药夺去性命。“宋刘亮合仙丹,须白蟾蜍、白蝙蝠,得而服之立死。”大概是获得了太多类似的教训,中国人逐渐知道了蟾蜍不宜食用的特征。如《茅亭客话》便记载:“顷有一士人好食鳝鱼及鳖与虾蟆,尝云此三物不可杀,大者有毒杀人,虾蟆小者亦令人小便秘脐下憋疼,有至死者。”而使得刘亮丧命的白蟾蜍也被赋予了灵异的特征,如在后蜀将要被北宋灭国时,“有村夫鬻一白虾蟆。其质甚大,两目如丹,聚视者皆云肉芝也。有医工王姓失其名,以一缗市之。归所止,虑其走匿,因以一大臼合于地。至暝,石臼透明如烛笼。王骇愕遂斋沐。”
比起这些灵异的传闻,蟾蜍在我国的文房文化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最常见的便是蟾蜍造型的研滴(一种滴水入砚的文具)。据说北宋宰相章惇就有一个铜蟾蜍研滴,“每注水满中,置蜍研仄,不假人力而蜍口出泡,泡殒则滴水入研,已而复吐,腹空而止。”著名的收藏家和严重洁癖哲米芾见到了也是欢喜不已,甚至是想用大量的古籍与之交换而不可得。《西京杂记》中的记载便提到在发掘晋灵公的墓时,发现了“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如新玉,取以盛水滴砚”,可见蟾蜍型的滴砚早已是我国的一项文化传统。
至少,在伪装成蟾蜍后,我们的旅行青蛙不再需要担心生命受到威胁,而且除了保命外,青蛙的蟾蜍伪装甚至能让它在临安城获得一份魔术师助手的兼职。据说在宋代的临安城,街头的幻戏师们会表演一种名为“蛤蟆说法”的戏术:“虾蟆九枚于席中置小墩,其最大者乃踞坐之,八小者左右对列,大者作一声,众亦作一声,作数声,亦如之,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点首作声如作礼状。”看来,即使吃光了我们给予的食物,也不用担心旅行青蛙在游览临安的时候饿肚子了,没准还会发回它在街头表演的明信片。

宋代 纺车图 注意小孩手中的蟾蜍
关于青蛙与蟾蜍的宋代都市传说
旅行者总会听到一些当地人诉说的奇闻异事。我们的旅行青蛙大概也会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驻足在西湖边的荷花上,聆听着湖中的老青蛙向它讲述发生在他们同类身上的宋代故事。
也许是针对当时江南普遍的食蛙习俗,青蛙开始成为一些带有佛教戒杀喻意故事的主角。在宋代的志怪笔记《睽车志》中遍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钱仲耕郎中佃任江西漕按部,晚宿村落,梦青衣数百哀鸣乞命。明日适见鬻田鸡者,感梦,买放,倾笼出之,其数与梦无差。”故事中的青蛙们以一袭青衣的形象出现在了钱仲耕的梦中,这种形象设计倒也是相当符合青蛙的外貌特征。
而有关蟾蜍的怪异传说在宋代更是层出不穷。相传在徽宗治国的宣政年间,黄河决堤,难以掩塞。一个名为牢吉的河清卒在被河水冲坏的土堰旁来来回回巡视,希望能找到重新堵上溃堤的对策。在巡视中,他听见似乎有人在呼喊他的名字,顺着声音的来源,牢吉进入了一片葭苇丛间,这才发现声音来自于一只等人高的大蟾蜍,牢吉不禁吓得拜倒在地。蟾蜍问:“尔数往来何为者?”牢吉将河决不可塞的情况如实告诉了它,蟾蜍随即吐出一个如同生离支一样的东西交与牢吉并说到:“吞此可没水七日,即能穷堰决之源。或有所睹,切勿惊也。”而当牢吉反应过来想要答谢时,早已不见了它的踪迹。
这则故事十分有趣地将蟾蜍的水族形象与治水工程串连了起来,大蟾蜍助人塞河,形象十分积极。然而作为一种在中国文化意义上较为复杂的生物,蟾蜍精作祟害人的传说在宋代也被口耳相传,《说郛》中便提到:
一吏人家女病邪,饮食无恒,或歌或哭,躶形奔驰,抓毁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结坛场,鸣鼓,吹禁咒之。次有一乘航船者,偶驻泊门首河内,枕舷卧,忽见阴沟中一蟾蜍大如椀,朱眼毛脚,随鼓声作舞。乃将篙拨得,缚于篣板下,闻其女呌云:“何故缚我壻。”船者乃扣门语其主曰:“某善除此疾。”主深喜问其所欲云:“秪希数千文,别无所求。”主曰:“某惟此女偏爱之,前后医疗已数百缗,如得愈,何惜数千耶?愿倍酬之。”船者乃将其蟾以油熬之,女翌日差。
故事中蟾蜍精惑女的情形十分形象地印证了那句“瘌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俗语,只是故事的最后,精明的航船人捉住蟾蜍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而蟾蜍主人公却变成了一滩蛤油,不禁令人捧腹。
不知各位蛙爸蛙妈们是否已经开始为蛙儿子准备一次宋代之旅了呢?
本期编辑 郦晓君


 朗读本文
朗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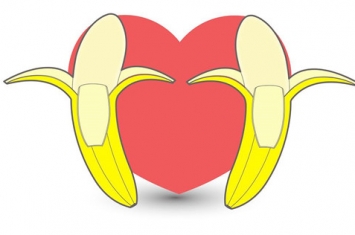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